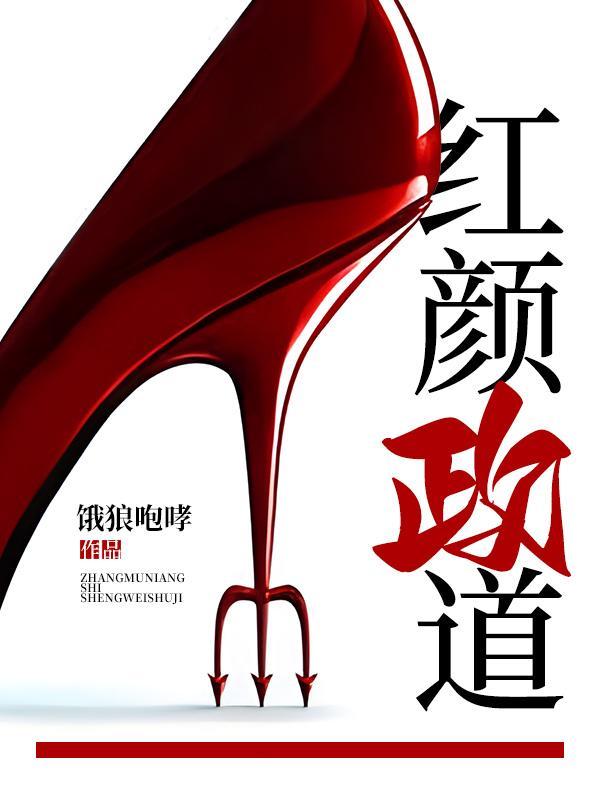宝书网>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50章 改变(第3页)
第150章 改变(第3页)
医院在重症病房播放经过调制的《静默之前》片段,帮助病人缓解疼痛;
联合国将每年三月十七日定为“全球倾听日”,号召人们放下语言,用心感受彼此的存在。
而江临舟本人,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有人说他在亚马逊雨林建立了一所“声音学校”,教原住民孩子用自然万物作曲;
有人说他化名为渔夫,常年漂泊在怒江上,只为记录水流的变化;
还有人说,每逢月圆之夜,楚科奇荒原上的石碑会再次发光,而那个背着布偶熊的男人,总会悄然出现,将新的声音封入大地。
林婉秋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场暴雨中的京都庭院。她撑伞走过枯山水,看见他在石头间放置十二枚贝壳,每一步都走得极慢,像在完成某种仪式。她想喊他,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等她走近,那人已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张湿透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已经不再写歌了。
>我只是活着,作为一首歌。”
多年后,一位研究跨文化情感传播的学者在整理档案时,偶然发现一份未归档的录音带,标签上写着:
>《明天的歌》??试录版,2045年3月18日凌晨。
他好奇地播放。
起初是长达四十分钟的空白,只有细微的呼吸声。
然后,一声孩童的笑声响起,清脆如铃。
紧接着,是海浪拍岸,是风吹稻田,是城市清晨的车流,是教堂钟声,是母亲哄睡的低吟,是恋人分别时的拥抱,是老人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谢谢”……
所有这些声音,没有经过任何剪辑或修饰,就这样自然流淌,持续了整整六小时二十三分钟。
结尾处,一个男人的声音轻轻响起:
“你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什么都不懂,只会哭和笑。
但现在,我们学会了倾听。
所以,请继续听下去吧??
这是我们的歌,也是你的。”
学者听完,久久无法言语。他查看录音设备的时间戳,却发现日期栏显示为:
**2073年6月9日**。
他猛地抬头,窗外阳光正好,一只萤火虫正停在玻璃上,微光闪烁,宛如一个休止符后的第一个音符。
他知道,这首歌,永远不会结束。
因为只要还有人在听,明天就仍在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