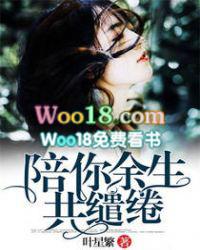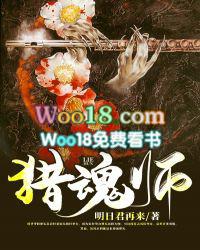宝书网>阎王下山 > 第1968章 不归海(第3页)
第1968章 不归海(第3页)
某个冬日午后,阳光正好,袁清漪坐在院中晒太阳,手里握着那枚早已失去光泽的玉佩碎片。忽然,一阵熟悉的气息拂面而来,她猛地睁眼,只见院门口站着一个少年,约莫十六七岁,眉眼清俊,嘴角含笑,手中拿着一枝新开的梅花。
“婆婆,”少年温和地说,“有人托我给您送来这个。”
袁清漪浑身一颤,几乎不敢呼吸。
那笑容,那语气,那姿态……分明就是年轻时的苏文。
她接过梅枝,指尖触到花瓣的刹那,一股暖流涌入心间。她抬头再看,少年已不见踪影,唯有一阵风掠过,带来一句极轻的话语:
>“我没有走远,
>只是在每个愿意守护光明的人身上,
>多停留一会儿。”
泪水无声滑落,滴在梅瓣上,折射出七彩光芒。
当晚,袁清漪寿终正寝,面带微笑,手中仍紧握那枝梅花。
次日清晨,全岛梅树一夜齐放,香气弥漫百里。渔民远航归来,说曾在海上看见一道白衣身影立于云端,向东方深深一揖,随后化光而去。
江湖从此少了一个名字,却多了无数传说。
点灯会日益壮大,发展出“执灯使”制度,由各地推选正直之士担任,负责收集冤情、传递信息、监督执行。他们不持兵刃,只带一盏白灯笼,所到之处,官府避让,豪强低头。
更有甚者,某些曾经作恶的修士,在晚年主动前往点灯会自首,坦白过往罪行,请求将其名字列入“赎罪录”,以期死后灵魂得以安息。
世界并未因此变得完美,仍有贪婪、背叛、杀戮。但有一点变了??**作恶的成本变高了,沉默的代价变大了,而希望,开始生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
又三十年后,一位史官撰写《守夜纪事》,开篇写道:
>“昔有阎王下山,非为索命,实为还债。
>还天下苍生被践踏之尊严,
>还世间公道被掩埋之声音,
>还人心深处久违之勇气。
>其身虽隐,其志长存。
>故曰:阎王不在地府,而在人心。
>守夜之人,永不下岗。”
书成当日,全国九百座城池同时点亮长明灯,彻夜不熄。
而在那最偏远的山村,一个孩子趴在窗边,望着夜空中的星光,悄悄点燃了一盏小油灯,认真地在纸上写下:
>“我想当一个好人。”
灯焰跳跃,映照着他清澈的眼眸。
远方,似乎有微风拂过,带着淡淡的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