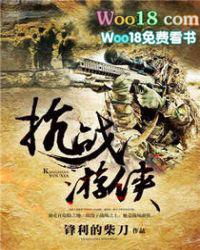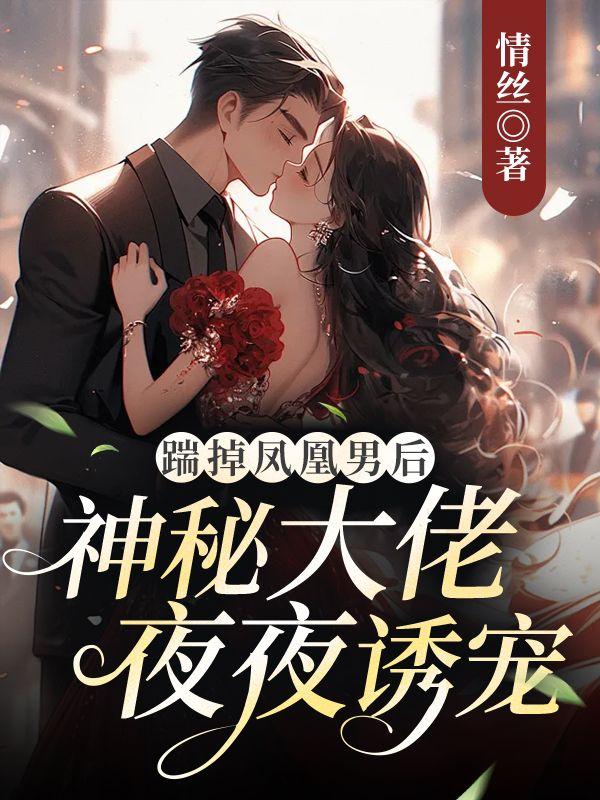宝书网>从离婚开始的文娱 > 第一千四百三十二章(第1页)
第一千四百三十二章(第1页)
从文化总局出来,午后的阳光变得柔和,透过车窗洒在谭越身上,带着初春的暖意。司机平稳地驾驶着车,行驶在长安街上,路边的玉兰花随风摇曳,粉白的花瓣偶尔飘落在车窗上,又被风吹走。
谭越靠在座椅上,脑海。。。
夜深了,城市安静得像被时间遗忘的角落。王乐天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晕圈住他面前那页稿纸,墨迹未干的最后一行字静静躺着:“他们没有名字,却撑起了一个时代的脊梁;他们未曾归来,却让星光照亮了回家的路。”他凝视良久,指尖轻轻抚过这行字,仿佛怕惊扰了其中沉睡的灵魂。
窗外风轻拂窗帘,带来一丝初春的凉意。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郊外看流星雨的那个夜晚。那时他还小,躺在草地上仰头望着天幕,父亲的手搭在他肩上,声音低沉而坚定:“乐天,你看那些闪过的光,不是随便划过去的。每一颗,都可能是有人用命换来的未来。”
当时他不懂,只觉得父亲的话太沉重,不像别的家长那样讲童话、讲故事。如今他终于明白,那不是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牺牲与守望。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林晚发来的消息:“小月今天在学校朗诵了你写的那段终章,老师录了视频,要我转给你。”
他点开附件,画面里,小月站在教室讲台上,穿着整洁的校服,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航天徽章??那是她爸爸生前单位寄来的纪念品。她站得笔直,声音清脆却带着一种超出年龄的庄重:
“他们没有名字……却撑起了一个时代的脊梁;他们未曾归来……却让星光照亮了回家的路。”
教室里很安静,同学们都抬头看着她,有的眼里泛着光。念完后,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爸爸走的那条路,也是王叔叔写给我们听的故事。”
掌声响起时,她没笑,只是认真地鞠了一躬。
王乐天闭上眼,喉咙发紧。他知道,这个孩子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等待父亲归来的女孩,而是一个开始理解“离开”与“留下”之间重量的人。
几天后,《等星星回家》正式杀青。最后一场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老观测塔拍摄。剧组特意选在凌晨四点开机,因为那是当年小月父亲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前,最后一次通电话的时间。
成年小月站在塔顶平台,手中捧着父亲遗留的军牌和那封从未寄出的家书。天空仍黑,东方微露鱼肚白。镜头缓缓推进,她的目光投向远方的地平线。
>【画外音】
>“爸爸,你说你要追星星。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非得是你去追?为什么不能留在家里陪我认星星?
>后来我才懂,有些人不追星星,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安心地抬头看星。
>你现在在哪一颗星上?是不是也在看着我?
>我把你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就像小时候你给我讲故事那样。
>原来,你一直都在讲同一个故事??关于责任,关于选择,关于爱却不常说出口的人。
>爸爸,我把所有星星都认全了。
>你可以回来了吗?”
话音落下,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洒在戈壁滩上,整片荒原仿佛被点燃。摄像机缓慢旋转,从她的侧脸转向辽阔大地,再徐徐升起,如同灵魂挣脱尘世束缚,飞向苍穹。
导演喊“卡”的那一刻,全场无人动弹。副导演摘下耳机,默默擦了擦眼角。吴工站在监视器后,久久未语,最后只说了一句:“成了。”
收工时,摄制组所有人自发列队,在观测塔前默立三分钟。有人带来了鲜花,有人放了一枚旧式军用水壶??那是当年基地技术人员最常见的随身物。王乐天将小月亲手折的一只纸火箭放在塔基旁,火红的尾翼在风中微微颤动。
回京的路上,他和林晚并肩坐在车后座,小月靠在林晚肩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枚军牌。车载广播正播放一则新闻:国家档案局宣布,将启动“沉默者记忆工程”,全面整理建国初期参与国防、科研、基建等隐姓埋名工作者的口述史,并向社会公开部分解密资料。
主播说:“这些人的名字或许从未登上报纸头条,但他们的足迹,早已刻进共和国的骨骼里。”
林晚轻声说:“我昨天去了爸爸的墓地。我把《沉默者家书》的DVD放进他的衣袋里了。我说,‘爸,现在有人记得你们了。’”
王乐天望着窗外流动的夜景,低声问:“你觉得,我们做得够吗?”
她摇头:“不是够不够的问题。是终于开始了。几十年来,太多人默默死去,连一句谢谢都没听到。我们现在做的,不过是把迟到的声音送出去。”
他点点头,忽而笑了:“你知道吗?前几天我翻老相册,发现一张小时候的照片??五岁的我站在新华书店门口,抱着一本《少年科学画报》,笑得满脸傻气。我妈说,那天我非要买那本书,因为我梦见自己长大了要写故事,讲给所有孩子听。”
“那你梦对了。”林晚看他一眼,“你现在就在做这件事。”
“可我不是为了这个开始的。”他说,“我是为了逃开我爸留给我的遗憾,才一头扎进写作里的。我以为远离他,就能活得自由一点。结果兜了一大圈,还是走回了他的路??用文字记住不该被忘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