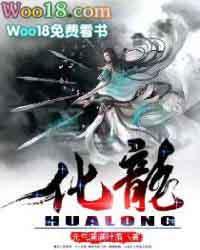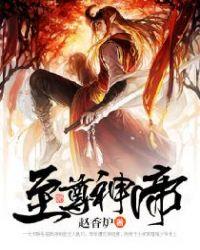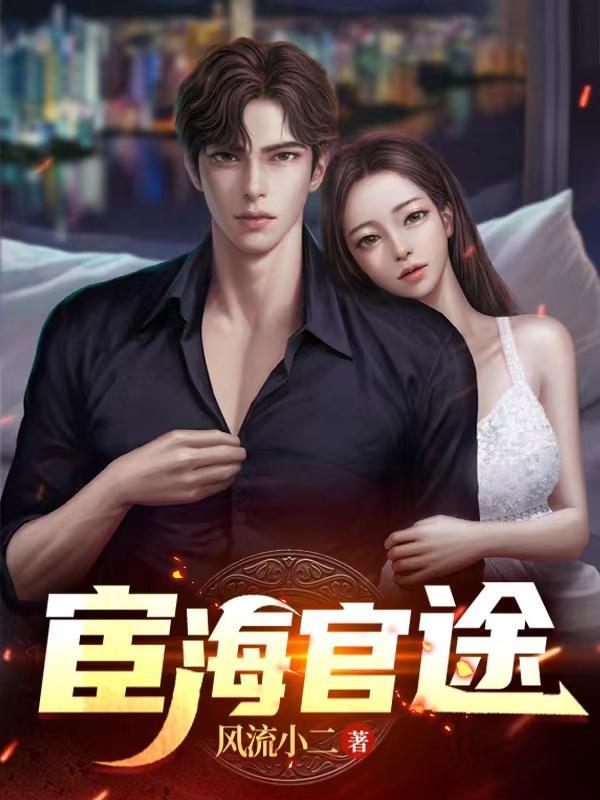宝书网>[三国同人] 金手指是看广告 > 第193章(第1页)
第193章(第1页)
谢乔没有直接辩驳经义,而是将尊贤和德政落到了实处,用梁国实实在在的变化作为论据。
一连串清晰的数字和事实,让原本准备引经据典反驳的几位名士,一时竟有些语塞。
巧言令色!一个略显尖锐的声音响起,来自侧席一位中年文士,乃是陈家一位旁支子弟,谢府君满口实效,数字详实,倒像是商贾计利,而非士人论道!此等效率之说,莫非是取法于商鞅、韩非?以奇技淫巧治国,恐非圣人之道,乃是霸道杂学,非我儒门正统!
这顶帽子扣得极重,直接将谢乔打入了非主流甚至异端的行列。
在场众人看向谢乔的目光,顿时又多了几分怀疑和警惕。
就在这时,谢乔身后沉默的毛玠霍然起身,对着那陈氏子弟拱手道:足下此言差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之道,非一成不变之死理。时移世易,政令亦当因时而变。《大学》亦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谢府君考察实效,正是格物致知,以求政令之善。何来奇技淫巧之说?至于选贤任能,更是《皋陶谟》所倡:知人则哲,能官人。不问出身,唯才是举,正是上合圣贤之意,下应百姓之盼。足下以法家、杂家相诬,未免武断!
毛玠引经据典,言辞恳切,将谢乔的政策巧妙地纳入了儒家可以接受的范畴,为她化解了方才的指摘。
场面一时有些僵持。
另一侧,一个面色阴沉的士人站起身,手中拿着一卷竹简,高声道:诸位,且不论梁国政绩真伪。我这里,倒有一物,或许能让诸位看清谢府君的真面目!
他展开竹简,厉声道:此乃梁国故吏冒死传出之密信!信中言明,谢府君得以在梁国站稳脚跟,实赖宫中常侍。其所用钱粮,皆是搜刮民脂民膏的不义之财!其与阉宦勾结,私相授受,此等行径,也配谈清流,也配谈圣贤之道?!
此言一出,犹如惊雷,整个厅堂瞬间炸开了锅。
与宦官勾结,这在自诩清流的士人眼中,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污点!
无数道质疑、愤怒、鄙夷的目光,如同利箭般射向谢乔。
,的局势变化,并未立刻表态,似乎在观察,在权衡。
持信人被谢乔一番抢白,堵得面皮涨红,讷讷退下,可这并未让风波平息,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浪涛。
先前那呵斥年轻人的陈氏子弟身侧,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缓缓站起。
此人乃颍川宿儒,颇有名望。
他轻咳一声,厅堂内安静了些许。
老者先是对着上首的荀俭等人微一颔首,而后转向谢乔,声调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威严:谢府君方才之辩,可谓伶俐。老朽听闻府君曾作《梁园赋》,文采斐然,传颂一时。只是此赋与府君平日行事风格大相径庭。坊间早有传言,此赋实乃他人代笔,谢府君不过沽名钓誉耳。
此言一出,比方才的密信更让一些人骚动。
对于士人而言,才学名声,有时甚至重于德行。
若连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假的,那这个人的一切都值得怀疑。
老朽自是不信,然人言可畏,三人成虎。
老者顿了顿,干枯的手指指向厅中悬挂的笔墨:今日雅集,名士云集。谢府君不若以此间景致,或以时局为题,当场赋诗一首?也好让我等开开眼界,见识谢府君真才实学,谣言不攻自破矣。
这要求看似给了谢乔一个自辩的机会,实则歹毒无比。
仓促之间,众目睽睽之下,要作出能匹配《梁园赋》水准的作品,何其艰难?稍有逊色,便坐实了代笔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