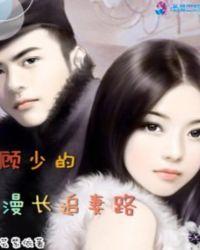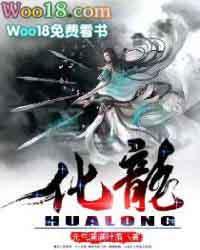宝书网>年代:大国崛起从工业开始 > 第456章 万亿次计算机集群先行验证方案(第1页)
第456章 万亿次计算机集群先行验证方案(第1页)
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星期,白杨几乎天天都在办公室内。
“银河一号”的资料库实在太过庞大,也太过超前。
每一个子系统,每一个模块,都蕴含着超越这个时代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设计思想和工艺结晶。
他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那无异于给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童一辆F1赛车,他根本无法驾驭。
他必须进行“降维”和“转译”。
这是一个痛苦而精细的过程。
他需要将那些基于未来工艺的HPC-CPU设计图,拆解成可以用现有“龙芯二号”作为基础,通过大规模集群阵列来弥补单核性能不足的过渡方案。
这需要重新设计集群的拓扑结构,重写底层的任务调度算法,确保数千颗“龙芯”能像一个统一的整体那样高效协同,而不是变成一盘散沙。
他需要将那匪夷所思的光互联网络技术,剥离出最核心、最基础的原理,设计成一个可以提前启动的“硅光技术预研项目”。
先不求一步到位实现芯片级光互联,而是从最基础的硅基光波导、调制器、探测器开始,为未来的技术爆发提前种下种子。
他甚至要将那个无所不包的软件生态,进行大刀阔斧地裁剪。
把那些最紧急、最关键的应用,比如高精度气象预报、流体力学仿真等,剥离出来,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攻关课题。
每一笔,每一次落笔前的沉思,都是一次艰难的取舍。
书桌旁的垃圾桶,一天就要倒两次,里面塞满了被揉成一团的废稿。
上面写满了各种被划掉的参数、推倒重来的架构图和逻辑流程。
七天。
整整七天的时间。
当白杨写下最后一个字,将笔重重地丢在桌上时,他整个人向后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他看着桌面上那厚厚一摞纸,眼中流露出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满足感。
成了。
通往“超级大脑”的攀登路线图,被他硬生生从未来“搬运”并“改造”到了现在。
即便如此,这也仅仅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框架和思路。
里面填充的,是各个阶段的核心目标、技术方向和关键节点。
至于每一个具体的技术细节,每一个参数的实现,还需要赵振华他们那群顶尖的头脑,用无数个日夜的汗水和智慧去填满。
这不是白杨不愿意写,而是根本写不完。
那海量的信息,如果全部细化成可以按部就班执行的SOP(标准作业程序),恐怕需要一个数百人的团队工作好几年。
他能做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指明方向,提供“地图”和“指南针”,让他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可以心无旁骛地全力狂奔。
他站起身,身体因为久坐而一阵僵硬,踉跄了一下才站稳。
他走到窗边,猛地拉开窗帘。
午后的阳光毫无征兆地涌了进来,刺得他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
适应了片刻,他才看清窗外的景象。
研究所里绿树成荫,有研究人员三三两两地走在林荫道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而祥和。
他走到书桌前,将那厚厚一摞手稿仔细地分门别类,整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每一个部分都用一个独立的文件夹装好。
做完这一切,他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通了助理办公室的号码。
“小李,来一趟。”
“好的,所长。”
几分钟后,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
“进来。”
助理小李推门而入,看到白杨的瞬间,不由得愣了一下:“所长,您……您没事吧?”
眼前的白杨,虽然换了干净衣服,但那股子掩饰不住的憔悴,还是让小李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