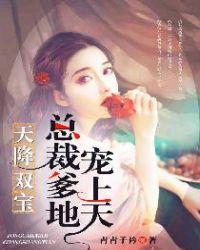宝书网>年代:大国崛起从工业开始 > 第370章 导演了一步好戏第一步已经完成(第2页)
第370章 导演了一步好戏第一步已经完成(第2页)
“很多报告的结论都是‘该区域煤层较薄,品位不高,无工业开采价值’,或者‘构造复杂,勘探难度大,建议暂缓’。咱们真的能从这里面找出新的大煤田?”
白杨拍了拍他的肩膀:“小钱,地质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过去的‘无价值’,不代表现在和未来也没有价值。当时的技术手段、勘探深度、评价标准,都和现在不同。更何况……”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堆积如山的资料,“信息只有在被关联、被重新审视时,才可能爆发出新的价值。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这些沉睡的信息一个‘被重新审视’的机会。”
这番话半真半假,既是给手下打气,也是在给自己构建“合理性”。
他心里清楚,大部分资料确实没用,但他需要这个“寻找”的过程。
接下来的日子,白杨几乎是泡在了这个临时的资料室里。
他表面上和大家一起整理、阅读,实际上,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几个他心中早已“锁定”的区域相关的资料上。
他特别关注那些描述地质构造、沉积环境、古地理面貌的报告,哪怕是只言片语。
他需要找到一些能够和他“新理论模型”挂钩的蛛丝马迹。
这个所谓的“新理论模型”,是他精心“编造”的。
核心思想是结合了前世七十年代末期,国际上刚刚兴起的一些关于板块构造理论,在聚煤盆地形成中作用的初步探讨。
现在这个年代,国内对板块理论的接受和应用还在起步阶段,正好适合他这种“超前”半步的发挥,以及对特定沉积相与优质煤层形成关系的深化理解。
听起来很唬人,也很“前沿”。
但仔细推敲,又似乎与现有的地质理论并不完全矛盾,更像是一种新的视角和综合分析方法。
“小钱,你看这份报告。”一天下午,白杨拿起一份关于晋西北某区域的早期勘探简报,指着其中一段描述:“这里提到,钻孔在穿过二叠纪石盒子组地层时,遇到了厚度不大的劣质煤线。”
“伴生有典型的沼泽相沉积特征的岩石组合。当时的结论是煤层不稳定,找煤前景不大。”
小钱凑过来看了看,点头道:“嗯,报告上是这么写的,这很常见啊,很多地方都有类似情况。”
“但是……”白杨的语气带着一种引导性:“你再结合这份关于华北板块古构造演化的初步研究报告,看看这个区域在晚古生代的古地理位置,是不是可能处于一个大型坳陷盆地的边缘,或者是一个长期稳定沉降的次级洼地?”
小钱皱着眉头,拿起另一份报告,又翻出相关的地质图。
比对了半天,有些迟疑地说:“呃……从区域构造上看,似乎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个区域的后期构造运动比较复杂,很多证据都被破坏了……”
“对!复杂!”白杨继续说道:“但也正因为复杂,早期的勘探可能只揭示了冰山一角!”
“你想想,如果这是一个大型的、长期稳定的聚煤沼泽环境,会不会在盆地的中心,或者构造相对稳定的区域,发育出厚度更大、品质更好的煤层?”
他进一步引导:“早期的钻孔,可能只是打在了盆地的边缘,或者因为技术限制,深度不够,没有打穿真正的主力煤层。”
“而这份报告里提到的‘沼泽相沉积’,恰恰是优质煤层形成的有利环境指示!”
白杨将几份看似不相关的报告、图件放在一起,用他那套“新理论模型”进行串联解释。
一个“被忽略的巨大潜力区”的轮廓,似乎就这么“合理”地浮现了出来。
小钱听得眼睛发亮,又带着几分将信将疑:“所长,您的意思是……这个被认为没啥价值的区域,可能……藏着一个大煤田?”
“我不敢肯定。”白杨立刻收敛起兴奋,恢复了严谨的科研态度,“这只是一种基于现有资料和理论推导的‘假说’。”
“但我觉得,这个假说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验证。”
“特别是这里提到的几个构造相对稳定的区块,如果能有更详细的地球物理勘探数据,或者重新进行一些关键点的地质填图和钻探验证,可能会有重大发现。”
这番话,既指明了方向,又留足了余地。
将“功劳”归于对现有资料的“重新解读”和“理论创新”,完美地掩盖了他“未卜先知”的真相。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白杨用类似的方法,又“挖掘”出了另外一两个“潜力区域”的线索。
其中一个指向了内蒙古东部的某个盆地。
每一个“发现”,他都完美地构建了逻辑链条,找到了相应的佐证材料(哪怕是些边角料信息),并用他的“新模型”进行了包装。
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白杨让小钱等人将这些“初步研究成果”整理成一份图文并茂的报告,重点突出其“理论依据”和“潜在价值”。
当然,也明确指出了这仅仅是“推测”,需要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