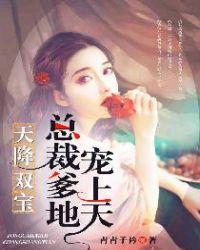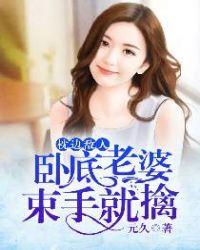宝书网>葬明1644 > 第114章 理由(第2页)
第114章 理由(第2页)
李之纲张了张嘴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已经是彻底的无语了。
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开始怀念起,路应标和杨彦昌在襄京时候的日子了。
那两位爷虽然张狂跋扈,桀骜难驯,但毕竟不是那么的聪明,只要伏低做小,给足对方面子,那么李之纲是可以通过引导等方式,让这两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事的。
并且,冯养珠和杨彦昌两人,除了管自己要钱要粮之外,官府里的事情也懒得管。李纲只需要给这两人伏低做小就行,其他时候,依旧是下荆南道最大的上官。
而眼前这位韩再兴韩大帅,对自己倒是客气和尊重,没事还给自己送一些上等烟草、高档肥皂,以及青云楼筹码什么的,但也仅限于此了。
襄樊营是不管自己要粮饷了,因为整个襄京府都被襄樊营牢牢的抓在了手中,根本不需要自己越俎代庖。
韩复还通过巡城兵马司、厘金局、中军衙门等设置,几乎将官府的职能都给架空了。
当然了,诸如调解民间纠纷,判案子等麻烦事情,还是由官府来负责的,只是这些事情,由襄京府和襄京县两级官府处理就行了,也不需要李之纲操心。
李之纲这个防御使,反而几乎没啥事可干。
如果只是单纯地没啥事干倒也好说,至少还能落得个清闲,可偏偏韩大帅又是个“雄才大略”的主儿,每每都惊天动地之举。
这些惊天动地之举,事前绝对不会和自己商量,但事后却总需要自己这个防御使出来背书。
就比如现在这样。
让李之纲觉得,路应标、杨彦昌和冯养珠这些人,都变得可爱起来。
“绿。。。。。。”
那边,杨士科看眼前这个文书越看越眼熟,想了想说道:“你是。。。。。。你原先是县学的那个书手,叫。。。。。。叫。。。。。。”
“劳父母大人垂问,学生乃是本县童生,名唤陈孝廉,原在县学等处以文字糊口,今为襄樊营中军衙门文书室主事。”陈孝廉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肘部缀有补丁的蓝袍。
脸上有了油水,气色不像之前那样蜡黄,只是头发还是有些乱蓬蓬的。
“对,就是陈孝廉。”杨士科满脸的诧异:“你怎地到襄樊营来了?”
对于这个年代的读书人来说,在丘八手底下混饭吃,总归还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
尤其还是在大顺丘八的手底下。
杨士科对韩复没有意见,但这时的风气就是如此,哪怕他自己也是大顺的官员,也不影响这个结论。
韩复面带微笑的看着这两人说话,并没有出言制止或者参与进来。
他想看看陈孝廉是如何应对的。
伴随着自己队伍的扩大,将来加入到这个集体当中的文人读书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大家提前适应一下也好。
陈孝廉要是能给杨士科等人打个样,那就再好不过了。
陈孝廉眼神下意识地有些躲闪,但转瞬之后就恢复了澄澈清明,他头还是微微低着,但语气却无比地坚定:“学生读圣贤书二十余载,在活三十有六,既无匡世救国之才,又无齐家糊口之计。老母妻儿饥馑冻馁,十数年来无
一日可称无忧。学生在县学写字糊口,亦是,亦是受百般奚落,个中酸楚,实在,实在是难以言说………………”
说到这里,陈孝廉眼眶通红,但语气却更加的坚定起来:“学生是四月间到的襄樊营当的书手,当时还是兵马司。兵马司中无人因学生穷酸而奚落欺侮学生,反而人人见重于我。到了中军衙门之后,韩大人亦不以小人才疏学
浅为意,委以文书室主事之重任,参与机要,预谋军务,小人这才知平生所学,原来不是全无用处。知遇之恩,良马尚且图报,况乎学生哉!”
陈孝廉声音渐渐变大,直房内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过来。
陈孝廉深吸一口气,接着说道:“自四月间,学生登记前来从军报名者一千有奇,其中流民超过八成,这些人若不是到我襄樊营中来,早已不知死在何处。而今日却皆成为忠诚骁勇的好汉。自入文书室来,只是经学生之手发
出的文书就可知,襄樊营就在吕堰驿、双沟口、震华门、张家店、宜城等处,设置过粥棚,施粥十数万碗,活民无算。襄樊营又在各处遍设工坊,如今已有工人千余口,每口不仅能有饭吃,亦可有工钱养家,此举又是活民无
算。”
说到这里,陈孝廉终于抬起了头,望向杨士科,有些激动的说道:“杨大人问学生为何到襄樊营来,这便是理由!”
好,说得好!
韩复忍不住在心里,为陈孝廉刚才的话拍手鼓掌。
他刚才还在为自己厚黑无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而有点小小的鄙视自己呢。
结果听完陈孝廉的话,韩复才意识到,原来咱韩再兴也是浑身上下,充满了人文关怀,充满了人性光辉的大善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