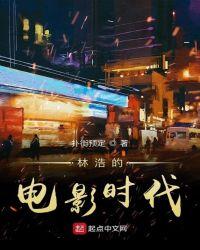宝书网>晋末芳华 > 第五百一十二章 各怀心思(第2页)
第五百一十二章 各怀心思(第2页)
翌日清晨,他召集所有听钟使者,宣布启动“百谣计划”: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母亲哄睡的呢喃、工人收工时的口哨、盲童摸索琴键的试探、渔夫撒网前的呼号……无论美丑,不论技巧,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表达,都将被纳入全球共感网络。
第一批提交的作品多达四万两千余条。其中有维吾尔族老人用热瓦普弹奏的思念之曲,藏区牧童对着雪山喊出的名字,乌克兰战地记者录下的防空洞里孩子们背诵诗歌的声音,甚至还有一段来自日本福岛核灾区的静默??整整五分钟,只有风吹过废屋窗棂的呜咽。
当这些声音被同步释放进共振场时,奇迹发生了。
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监测员发现库内温度自动下降0。8℃,且所有冷藏舱壁表面凝结出细密水珠,排列成类似五线谱的图案;太平洋底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无人探测器捕捉到一群深海鱼类集体向上游动,形成巨大的螺旋队列,其运动轨迹与《月光谣》与《土谣》叠加后的合成波形完全吻合;而在喜马拉雅山脉某处冰川内部,地质雷达扫描显示出一座疑似人工结构的空腔,内部回响持续不断,初步判断为某种大型乐器残骸,年代测定接近公元四世纪。
“又一个‘钟穴’。”林奈看着三维成像图,手指微微发抖,“和长安地窖一样,只是这次藏在雪山之心。”
探险行动迅速筹备。由六名听钟使者组成的科考队携带便携式共振仪深入冰川,历时十七天抵达目标区域。他们在冰层下三百米处凿开通道,果然发现一间封闭石室,中央立着一口倒悬的青铜巨钟,高约三米,表面蚀刻满星图与古篆,钟口朝上,宛如承接天露。
最奇特的是,钟体内壁布满蜂窝状小孔,每个孔中嵌有一粒晶莹剔透的“声核”??经鉴定,成分与小满化光后遗留的蓝色结晶完全相同。
当一名队员无意间轻敲钟身时,整座冰川开始共振,雪峰顶端腾起一道彩虹色光柱,直冲云霄。与此同时,听钟台所有设备同时接收到一段清晰信息:
>“钟非一人所铸,音非一时而成。千年一醒,只为唤尔归心。”
文字消失后,紧接着传来一段旋律??既非《月光谣》,也非《广陵散》,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复合乐章,融合了西北民谣的苍凉、江南丝竹的婉转、西域胡乐的奔放、南岛歌谣的轻盈……仿佛将整个人类文明的音乐记忆压缩成一首安魂曲。
陈默跪倒在地,泪流满面。
他知道,这不是小满单独传递的信息。这是千年来所有未能说完的话、所有被战火焚毁的诗篇、所有含恨而终的吟唱,借由这口钟汇聚成声。每一个曾经用心听过世界的人,此刻都在其中发声。
一个月后,全球同步举行“归音仪式”。在长安、开罗、墨西哥城、悉尼、圣彼得堡……数百万人同时关闭电子设备,静坐聆听周遭最原始的声音:风吹树叶、水流石上、婴儿啼哭、老人咳嗽、恋人低语、朋友大笑。
那一夜,地球磁场出现罕见平稳状态,电离层扰动降至百年最低,连太阳风撞击大气层产生的极光也呈现出规则的环形结构,颜色由绿转金,持续整整一夜。
而在南极洲边缘,一支中国科考队意外发现一处地下洞穴系统。洞壁覆盖着远古壁画,描绘的正是历代“调钟者”:晋末披麻衣的柳元度、唐初持玉磬的女道士、明末抱着瓷瓮的老匠人、民国背着留声机的学者……最后一个人影模糊不清,唯有手中物件轮廓分明??是一台老旧录音机。
壁画下方刻着一行字,使用现代汉语:
**“下一个,是你吗?”**
消息传回听钟台那天,陈默正在教一群孩子辨认风中的声音。他抬头望天,乌云密布,雷声隐隐。
一个小女孩拉住他的衣角,仰头问道:“陈老师,如果有一天你也走了,我们会记得你吗?”
他蹲下来,轻轻抱住她,“不用记得我。只要你们还愿意听,我就一直在。”
话音刚落,第一滴雨落下。
紧接着,万籁俱寂中,一声清越的钟响自远方传来??不知来自哪座深山古寺,还是某人心底。
雨越下越大,可没有人离开。孩子们手拉着手,站在屋檐下,齐声哼起那首还不太会唱的《土谣》。
他们的声音很轻,却穿透了雷鸣。
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有人停下争吵,有人放下武器,有人拨通多年未联系的电话,有人终于说出那句“对不起”,有人紧紧抱住身边的人,久久不愿松开。
钟声仍在继续。
它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
它就在这一刻,在每一次真诚的倾听里,在每一颗愿意被打动的心中,缓缓升起,永不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