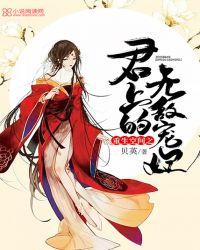宝书网>忽悠华娱三十年(马寻全集免费看 > 第七百三十九章 师师的人间至乐人在囧途钢的琴杀进贺岁档(第4页)
第七百三十九章 师师的人间至乐人在囧途钢的琴杀进贺岁档(第4页)
瓶内百舸争流,纸船密布,而这一只与众不同,轻轻振翅,竟在瓶中盘旋一圈,仿佛欲破空而去。
十年过去。
“写作与遗忘”
课程已成为全国教育改革典范,数百所学校设立同类课程,统称为“心灵书写计划”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情感重建工程”
的核心项目之一。
而在民间,一种新的仪式悄然兴起:每年春分之夜,人们聚集在开阔之地,共同书写一封信,随后投入篝火。
火焰升起时,常伴有轻微嗡鸣,天空偶现流星状光点,划破云层,似有回应。
科学家依旧无法完全解释这一切背后的物理机制,只能提出假说:“情感信息可能以量子纠缠态形式存在于宇宙背景场中,当集体意图达到阈值,便会触发可观测效应。”
但百姓不在乎理论。
他们只知道,自从不再执着于“收到回信”
,反而越来越多的人声称“感觉被听见了”
。
某个深秋傍晚,苏晚接到一通跨国视频电话。
来电者是一位金发女子,操着生涩中文:
“您好,我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心理实验室的研究员艾米丽?冯。
我们监测到,过去一年间,全球范围内与‘孤独’相关的自杀率下降了41%。
抑郁症患者自我陈述中,提及‘感到被理解’的比例提升了68%。
我们追踪数据源头,发现所有异常波动都指向同一个关键词??‘信’。”
她顿了顿,眼中泛起泪光:“三个月前,我母亲去世了。
我一直没能说出‘我爱你’。
但在她葬礼当晚,我写了一封信,照着网上教程烧给了风。
第二天清晨,我家院子里开出一朵从未见过的花,花瓣透明,上面浮现出一行字:‘我也爱你,傻孩子。
’”
镜头转向窗外??那朵花仍在,静静立于石缝之间,宛如琉璃雕琢而成。
苏晚沉默良久,最终只说了一句:“欢迎加入这场对话。”
挂断电话后,她翻开最新一期的学生作业集。
一篇名为《我和另一个我吵架了》的文章引起她的注意:
>“我觉得现在的我很讨厌。
懒惰、胆小、总爱假装坚强。
所以我写信骂了过去的自己。
我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努力?为什么要讨好所有人?为什么不敢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