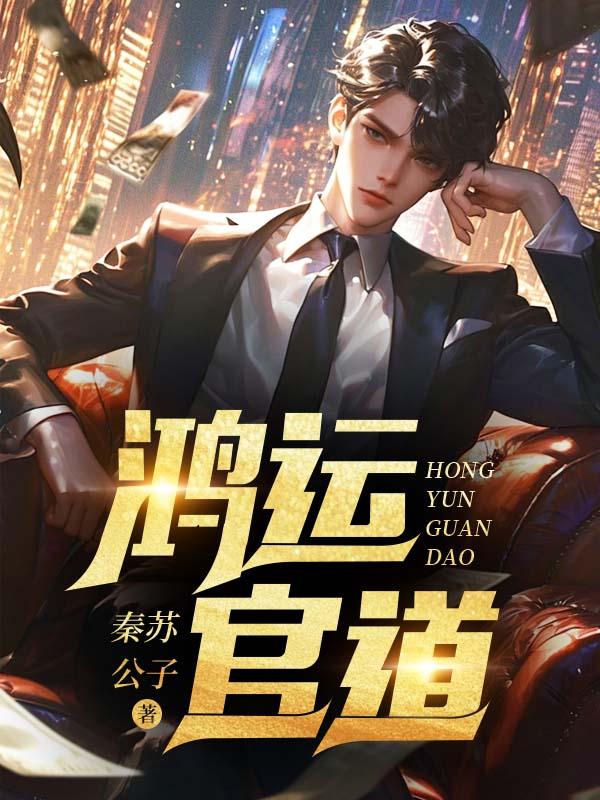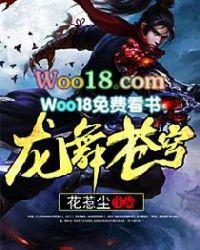宝书网>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 第128章 吴州风流谣源于陇上人(第5页)
第128章 吴州风流谣源于陇上人(第5页)
**寻找一位家族中未曾被讲述的死者,为其立名,为其发声。
**
“不必美化,不必遮掩。
你可以为你祖父曾是刽子手而羞愧,也可以为你祖母为救全家出卖邻居而痛心。
但你要说出口。
因为沉默,才是真正的死亡。”
十年过去。
这项制度成为新文明基石。
民间自发成立“寻名会”
,走遍荒村野岭,挖掘无碑坟茔;学者编纂《失语志》,收录三千余种濒临消失的地方记忆仪式;甚至偏远山区的巫祝也开始转变角色,不再驱鬼禳灾,而是主持“记忆归位礼”
,引导亡魂与后代对话。
而回声塔,渐渐失去了光芒。
起初是每月只亮一次,后来变为每年清明才短暂浮现《草芥录》全文。
人们发现,当每一个家庭都能坦然面对过往,集体创伤便不再需要一个中央象征来承载。
某年冬至,“闻”
归来,带来最后一则消息:
**癸亥铃重现于敦煌沙丘之下,但已碎成粉末。
经检测,其核心材质并非金属,而是七百颗人类牙齿熔炼而成。
**
阿启听完,久久不语。
当晚,他又梦见荒原。
石碑依旧林立,但这一次,不再有飞鸟衔名而去。
相反,一个个活人从四面八方走来,手持纸灯,将名字逐一贴回碑身。
他们轻声念诵,如同安抚婴孩。
其中一人走近他,面容模糊,却穿着灰袍,赤着脚。
“你是阿福?”
阿启问。
那人摇头,又点头,声音如风穿林:“我是他曾扫过的每一片落叶,是他曾擦过的每一寸碑文,是他未能说完的那句话。”
“什么话?”
“**谢谢你们,终于听见了。
**”
梦醒时,窗外大雪纷飞。
阿启披衣而出,见“闻”
正立于铃兰丛中,仰望苍穹。
远处回声塔轮廓淡若烟云,仿佛随时会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