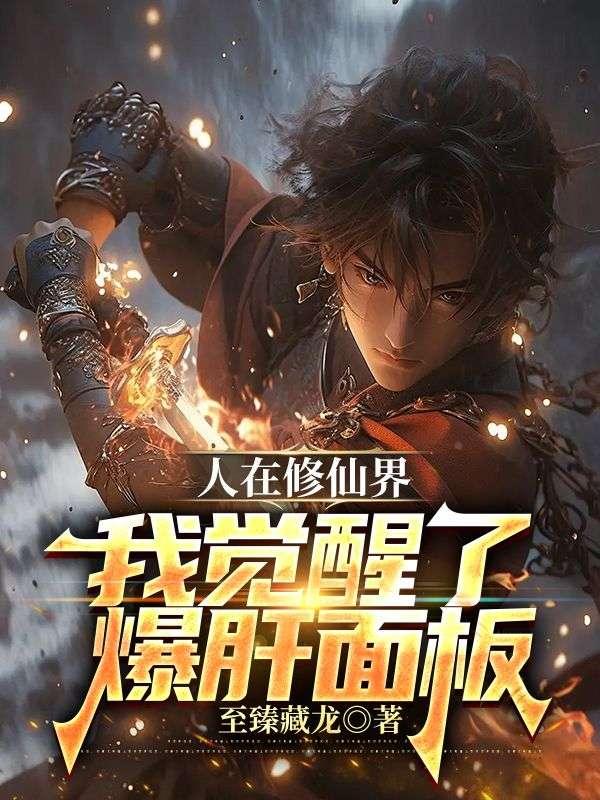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大侠別急,笑傲江湖先问问大明律 > 第315章 江湖郎中(第3页)
第315章 江湖郎中(第3页)
方管事带来一人,那人径直走入书房,大声道:“云积,久违!”
路平大吃一惊。
张居正竟然派了他的儿子,自己那位眼高於顶的同年,榜眼郎张嗣修微服来访。
张嗣修生得很是俊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他打量了一下书房的陈设,笑道:“云积理江湖事,倒是如鱼得水。”
“思永兄为翰林清贵官,何必羡此劳碌身!”路平淡淡道。
方管事为二人奉上清茶,便悄然退下,这是一个极其懂事的人。
路平暗自感受屋外动静,待证实確实无人之后,神色便放鬆下来。
“虽是同年,一向少有亲近。不知思永兄此来,可是阁老有什么吩咐?”
张嗣修面色一沉,苦笑道:“家父见云积屡屡建功,竟是將他以为绝无可能之事,化於无形,不时对我言道:『当年可是看走眼了。』”
路平微微一笑,张嗣修里说的就是衡州江湖事,这位相国果真是事无巨细都了如指掌,当日让路平去“衡州试试”,竟然真的试出了介入江湖事的办法。
“阁老曾言:“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於声名,毋尽拘於资格,毋摇之以誉毁,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告掩其大节。』人心难测,但得『功实』二字,便是得人。”
张嗣修微微一证,不禁面有色。
他深深看了路平一眼,嘆道:“不想云积经此歷练,果然学业大进。不过—知易行难·。。。。”
万历五年的同年之中,沈懋学和汤显祖名声最大,张居正极力笼络,沈懋学接受了张居正的邀约,而汤显祖却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
结果沈懋学成了那届的状元,汤显祖落第归去。
便是沈懋学,不久之后也与张居正父子反目,“夺请”中,他屡屡给张嗣修写信劝解。
张嗣修置之不理。
沈懋学这位心学门人,少年任侠,武技精湛,一把丈八长矛舞的虎虎生风,气得辞职还乡,不久就病死了。
也著实可怜。
当年,张居正父子何尝將路平这样的人放在眼里。
纵然知道一切以功实为准,实际中依旧是党同伐异。
两人閒谈片刻,便开始切入正题。
张嗣修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淡淡道:“云积所为非常之事,此次大计,勿要担心。”
短短一句话,便让路平又轻鬆了几分。
“明年举国清丈田亩,江南为重,河南为难,云积可有什么主意?”
江南为重,是说赋税多出於江南,江南地主或是豪强,或是受豪强庇佑。
河南为难,是说河南一带,帮派眾多,或为清丈隱忧。
两处都依赖豪强,但江南的豪强,是以退休官员为主体。
而河南的豪强,却是江湖帮派撑起了保护伞。
“我思河南之事已久,只是体制所限,容不得我到河南生事。”
路平沉吟著说道。
“此事不难,家父以有主意。”
张嗣修笑道:“家父和內相商量,要设立一个新的衙门,处置江湖事务,云积以为如何?有人擬定了几个名字,家父都不满意。”
“六扇门!”路平脱口而出。
张嗣修一,抚掌笑道:“好名字。”
三法司,六扇门。
张嗣修品味了一下,越来越觉得这个名字颇有一番意思,不由得对路平更是刮目相看。
“家父原先想在刑部之下设立,刑部道与体制不合。又想在大理寺设立,大理寺倒是答应的爽快。只是,家父道:『云积资歷尚浅,不足以服眾。』,六扇门虽立,你要参与其事,怕是还要等等。”
云积不必担心,家父也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