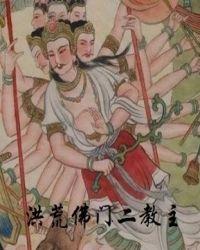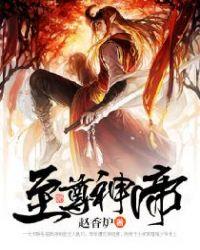宝书网>孕奴花妃传 > 第24章 上 藤原香子丰腴诗媚献身美人计权谋暗藏(第4页)
第24章 上 藤原香子丰腴诗媚献身美人计权谋暗藏(第4页)
“然……玉藻妃素体孱弱,常年多病。适才久立已觉疲乏,且此地人声鼎沸,恐不利娘娘静养。敢请大使恕罪,让她先回后宫安歇,可好?”
此言一出,殿堂内的目光齐齐看向我。
我未答,先回首与花妃们交换一瞥。黑蔷薇端坐席间,眉眼依旧冷冽,却轻轻一点头。她的眼神中分明写着:这一步该顺水推舟,不必生枝节。
我唇角微扬,转而望向玉藻妃。她面色苍白,确有些病态之美,粉发垂落,因劳乏而显得愈发楚楚。
我缓声开口,语调沉稳,带着分寸:
“陛下所言甚是。娘娘既需静养,自当早些安歇,勿再辛劳。行舟谨祝娘娘早日康健。”
玉藻妃微微欠身,虚弱的嗓音带着一抹感激:
“臣妾多谢大使体恤。”
随即,几名宫女上前,小心搀扶着她缓步退下。
殿门再度阖上,一缕清风自她离去的方向飘入,似乎也将殿中紧绷的气氛轻轻吹散。
随着玉藻妃退场,宴会再度热烈。
酒盏相击,清音回荡。
烛光摇曳,映得群臣脸庞时明时暗。
我在席间周旋,自然从容,举杯与众人交错,言笑皆有分寸。
酒过数巡,殿中热意渐盛,我轻轻一拍几卷书册,旁置的世界地图徐徐展开。
烛光下,那幅巨大的地图宛如展卷山河。群臣目光随之被牢牢吸引。
我缓缓起身,指尖轻点其上,声音清朗而铿锵:
“诸位观之,此乃天下之势。凡与我大唐修好,奉礼称臣者,邦交绵长,百姓安泰,商贾流通,衣食无忧。譬如西域诸国,倚我庇护,丝路繁盛,财货川流不绝。”
我又轻轻一拂,指向另一角,神色一凛:
“而那些不识时务,逆我天朝者,结局便不堪言。数年前,印度本是佛法渊薮,然因多次违抗,终在兵戎与教义交锋中日渐势微,佛土不复昔年之盛。至今,反而需依仗大唐,方能苟延。”
此言一出,殿中群臣面色不由一变。
我目光微沉,手指缓缓落在那片孤立于大洋之上的岛屿——倭国。
“至于贵邦——”
我停顿半息,举起酒盏,目光缓缓扫过殿中官员,唇角微扬,既似笑,又似不笑:
“在此幅天下图中,不过小小一隅。若顺天朝之势,和乐相处,亦可享太平。若逆而行之,便如狂澜击石,转瞬粉碎。”
群臣无不屏息,额角隐隐见汗。烛焰摇曳之间,酒气、威压与未言的锋锐交织,将整个大殿牢牢笼罩。
鸟羽天皇额上已有薄汗,却强作镇定,举杯高声道:
“唐国果真雄盛无双!朕与满朝群臣,皆愿修好,绝无二心!”
殿中群臣齐声附和,声浪如潮。我举盏未饮,缓缓落下,语声在殿堂中沉沉回荡:
“我观陛下心怀仁念,欲为万姓苍生免去兵戈之苦,诚乃明君也。此行舟敢在殿上直言:我大唐并不图你邦之田土,不索贡赋,不役兵卒,不徭纳粮。大唐所求,不过一份信义。”
群臣面色微动,窃窃私语。我的话语一字一句,清晰而锋锐:
“——自今往后,切莫怀敌意于大唐。若有一念叵测,后果自负。大唐并不喜灭国屠城,更不愿见种族泯绝。然天下之事向来由不得心,往昔有些愚昧小邦之主,口里一套,背后一套,诈而不忠,见利忘义,终至亡国灭宗,血流漂杵。此等下场诸位当以为戒。”
殿中空气陡然一滞。
烛焰颤抖,照出百官额上的细汗。
他们已亲眼见过“琉光天玺”,那晶莹剔透、似神迹的国玺;见过那册煌煌巨制,仿佛能包纳天地的图鉴巨书;更见过牡丹赤手空拳,以三招摔碎弁庆之威。
如今我言辞虽和缓,却如雷霆,昭示出大唐既有灭国之能,也有宽仁之心。
鸟羽天皇端坐御席,背脊却不自觉僵直。
他的双手在袖中紧紧握合,指节因用力而泛白,额角已渗出冷汗。
片刻之后,他终于俯首,声音微颤却竭力保持镇定:
“大使之言,鸟羽铭心刻骨!朕自承大唐乃天朝上国,德威并济,非我小邦可敌。此番得蒙唐王垂顾,已是万幸。今夕之后,朕即命中书,草定誓文,以金印为契,誓世代与唐修好,永不背离,世世子孙皆奉大唐为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