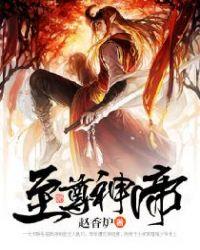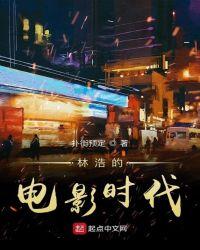宝书网>女帝,从招聘诸葛亮开始 > 120130(第26页)
120130(第26页)
说完,他重重地将头磕了下去。
诸葛亮看着他,脸上露出了欣慰而深邃的笑容。他缓缓起身,弯腰亲手将卢志云扶起:“将军迷途知返,善莫大焉。快快请起,从此以后,你我便是一家之臣,同心戮力,共创大业。”
他扶着浑身仍在微微颤抖的卢志云坐下,将那碗粥再次推到他面前:“现在,将军可以安心用膳了。吃完,亮还有周边城池的布防图,需与将军细细参详。我军下一步兵锋所向,还需将军这等熟知内情之人,鼎力相助。”
卢志云闻言,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震惊,随即化为无比的复杂和最终的了然。
这才是他真正的“投名状”,——
作者有话说:手腕腱鞘炎,做了手术,不好意思耽误了几天[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第130章消化磨合
等到诸葛亮回到县衙时,晨雾尚未散尽,县衙内一片初醒的忙碌,霍去病尉迟敬德正揉着惺忪睡眼,方才陆续到来准备开始一天的职事。
众人只见诸葛亮步履从容地自外而入,羽扇轻摇,唇角还带着一丝笑意。他已经从卢志云手里得到了余下四城的布防图。
现在姜戈只要看见丞相大人,心中就有无限的安全感,她好像忽然有点懂了刘阿斗的感觉——有这样一位智深如海、算无遗策、永远能在谈笑间将万丈波澜抚平的丞相在侧,确实很容易让人放下所有紧绷的心弦,产生一种“天塌下来也有高个子顶着”的踏实和……嗯,偶尔想要偷懒的安心。
这种安全感,并非来自于懈怠,而是源于对绝对能力的无限信任。
诸葛亮目光扫过姜戈,见她眼神清亮,神态安然,那唇角的笑意似乎又深了一分,微不可察地对她颔首示意。
一切尽在不言中。
说是不言,但诸葛亮还是要向姜戈说一下卢志云的情况。
话音刚落。
霍去病便问出了那个众人都很好奇的问题:“那我们乘胜追击?”
“兵不可妄动。”
他目光扫过堂中因得知获得布防图而略显兴奋的众人,缓缓道:“我军新胜,士气虽旺,然降卒待融,新城待抚。造纸工坊初具规模,新式农具、作物尚未推广普及。此时若再启战端,便是舍本逐末,如持漏瓮接雨,虽得滴水,终难满盈。”
“当下之要,在于消化二字。”诸葛亮一语定调。
自那日诸葛亮轻摇羽扇,定下“战略消化”之策后,整个县城便如同一架精密而高效的机器,在运筹帷幄的诸葛亮调度下,各个部件开始全力运转。
新划出的巨大校场,取代了往日农田的宁静,如今终日被震天的口号声、金属碰撞声和整齐划一的脚步声所笼罩。
这里,便是霍去病与白起共同执掌的“熔炉”。
他们两个的任务,是将原有的松阳县兵、卢志云带来的降卒,以及新招募的青壮,彻底打碎、融合,锻造成一支全新的铁军。
过程绝非一帆风顺。
降卒们初来时,大多面带惶恐、疑虑,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屈辱。他们自成一体,与松阳县兵之间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墙。毕竟曾经他们可都是吃皇粮的正规军,这些流民军队怎么能和他们相比较?
可偏偏他们输了。
而松阳县的兵则带着胜利者的优越感,看待这些“手下败将”时,难免有些趾高气扬。
这种微妙的对峙,在第一次合练时就爆发了。
霍去病崇尚的是骑兵的机动、闪电般的突击和战场上的临机决断。他训练的骑兵小队(虽然战马稀缺,多以竹竿代马练习)讲究散兵游击,迂回包抄,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杀伤和扰乱。
而白起,则是不折不扣的纪律至上主义者。他操练的步兵方阵,要求的是如山岳般的沉稳,如臂使指的绝对服从。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精准到毫厘,每一次前进后退都必须保持阵型的绝对完整。
在他眼中,个人勇武必须让位于集体的铁律。
这天,霍去病正让他麾下那些带着游侠儿气的“骑兵”进行穿插演练,队伍不可避免地冲撞了白起正在严令操练的步兵枪阵。
“乱哄哄成何体统!撞乱我军阵,依律当杖责!”白起面沉如水,声如寒铁。他身后的步兵方阵立刻停下动作,长枪顿地,发出沉闷的齐响,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开来。
霍去病打马而来,少年英气的脸上满是不以为然:“白将军,战场瞬息万变,岂能一味固守阵型?我骑兵若不能灵活机动,寻觅战机,与固定靶何异?”
“无纪律的灵活便是溃败之始!未得号令,擅自冲阵,乃军中大忌!”白起寸步不让,他的目光扫过那些略显散漫的“骑兵”,尤其是其中原属卢志云部的降卒,“乌合之众,不堪大用!”
这话刺痛了许多人。降卒们脸上泛起怒色,县兵们也觉得被地图炮波及,场中气氛瞬间剑拔弩张。
一直在一旁默默观察,协助维持秩序的卢志云,此刻眉头紧锁。他深知这两位的脾气和理念,也明白再争执下去,于练兵无益。他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对两位名将抱拳行礼,声音沉稳:“霍将军,白将军,请恕末将多言。”
两人的目光同时投向他。
“霍将军所言骑兵之利,在于动、在于快、在于出其不意。白将军所言阵战之威,在于稳、在于坚、在于合力一击。”
卢志云斟酌着词句,他多年的实战经验在此刻化为透彻的理解,“然,末将以为,二者并非水火不容。昔日在边军,末将亦曾见精锐骑兵与重步兵配合作战。骑兵扰敌侧翼,吸引注意,步兵方阵则正面推进,一锤定音。或步兵结阵固守,骑兵自两翼突击包抄……关键在于,如何让二者听懂彼此的号令,如左右手般配合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