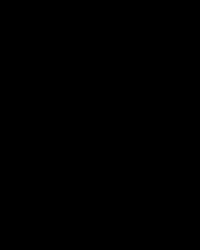宝书网>大明王朝1627 > 第135章 刚参加工作五年的卢象升(第4页)
第135章 刚参加工作五年的卢象升(第4页)
“朕看,这个问题,倒是不用问卢卿了。”
卢象升眼神一亮,拱手就要作答:“臣……”
“你是不必答这个问题了。”朱由检却将手一摆,打断了他的话。
他伸出一根手指,细细道来:
“其一,你言十万、二十万之数,是在试探朕有否平灭辽东之心,又对这桩军国大事,预期到了何种地步。”
卢象升的脸色瞬间一僵。
朱由检伸出第二根手指。
“其二,你言离任后贪腐再起,是在探究朕有否澄清吏治之志,而此‘吏治’,又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是到官员,还是通到胥吏。”
卢象升内心,已有些汗颜。
朱由检语速开始加快。
“其三,你言漕运空船之事,是在试探朕是否有整顿漕运,乃至变通漕运之心。”
“其四,田额不实,是在试探朕是否有清丈天下田亩之心!”
“其五,所谓兴农教事,是在试探朕是否愿在北直隶,再行农耕之事!”
朱由检说到这里,将完全摊开的五根手指在卢象升面前晃了晃,戏谑地问道:
“怎么?卢卿是以为朕没有读过《潞水客谈》,还是以为朕不知徐贞明、王应蛟、左光斗、徐光启诸公之事?”
一连串的名字,如同连珠炮一般从年轻天子的口中吐出。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代表着一段朝堂的往事,一番改革的艰辛。
卢象升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羞愧得无地自容,只能尴尬地拱手道:“臣……臣不敢。”
朱由检摇了摇头,脸上的笑容不知何时已经收敛得一干二净。
他没有再看卢象升,而是转身,一步步走回御案之后。
当朱由检缓缓坐上宝座之时,整个大殿的气氛仿佛都为之一凝。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自上而下地俯视着殿中的臣子。
明明还是那张十七岁的年轻面孔,可卢象升却从那双深邃的眼眸中,看到了一种与年龄完全不符的成熟与威严。
是天子威压带来的错觉吗?
还是帝王之家先天早熟?
可是先帝初登基时,也未曾有如此气势啊!
“卢卿,年轻人当有朝气,往后还是开诚布公一些吧,不要学官场前辈,作此中庸之举。”
话音落下,不带一丝波澜。
卢象升呆立当场,心中后悔不已。
唉,昨日拜访老师时,老师说什么‘新君年少,心思难测,当谨言慎行,多看,多听,少言’。
结果自己画虎不成反类犬,搞成了这四不像之举。
这下,恐怕是弄巧成拙了。
朱由检心中好笑。
二十七岁的卢象升啊,还真是稚嫩得很。
他淡淡道:“算了,先把马草一事说完吧。”
只听朱由检继续说道:“你的方案很好,但朕还得补充几点。”
“你说民间自用马草,三分之一用于烧火。”
“但你还未到任,恐怕不知永平府滦州盛产煤炭,此地两斤煤仅值一文。”
“永平百姓,用于炊薪的马草,未必有你想象的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