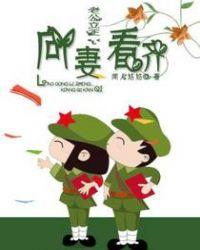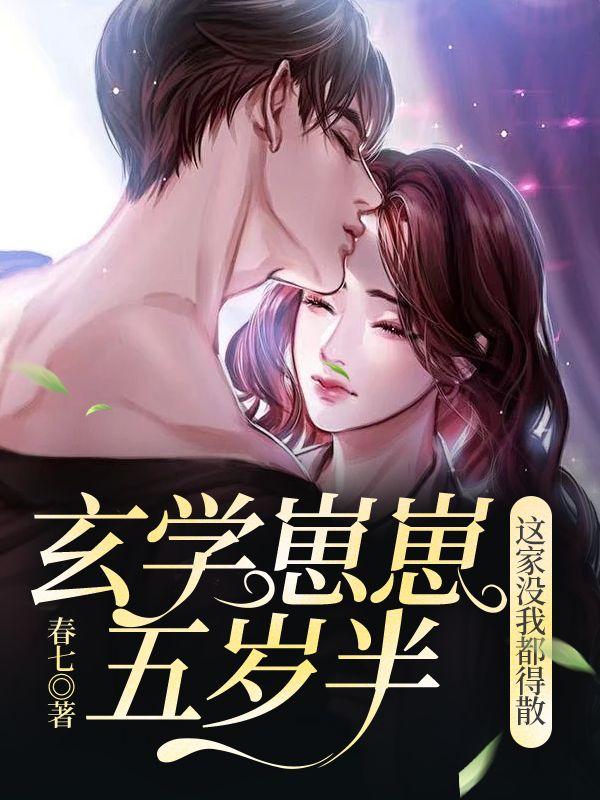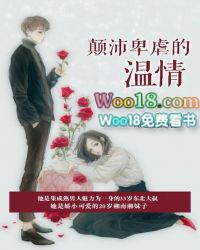宝书网>铁娘子她怎么登基称帝了 > 民力(第1页)
民力(第1页)
崇祯八年七月十一日,大同社向其治下十二郡广告《告万民书》,并颁布《民衔令》。
在《告万民书》中,大同社宣告授予天下百姓民衔,无论男女老少,皆获一级民衔“少士”,以感谢百姓辛苦劳作,供养国家。
获衔者,见官不拜,面圣不跪,如有人强迫,可上告公署。
《民衔令》则是对民衔名称、晋升要求、相关优待的具体规定,从“少士”至“大庶长”,共分十八级。
此一书一令公布,南楚顿时沸腾,几乎无人再关注严打贪腐员役之事。
天下也随之震动,给天下万民授衔,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爵位,尽管不能世袭、优待甚少,却是亘古未有之事,容不得绅民不热议。
实际上,民衔带给百姓的好处远不如大同社此前减租放奴等政策多,但热度却远远高于这些政策。
甚至真有人因此迁入大同社治下郡县,以享受这辈子都没敢奢望过的“贵族待遇”。
启明城为此举办了三日的庆祝活动,城里城外都热闹无比,连往日一贯清静的旅馆也喧哗不已。
王石放下《宝庆周报》,耳畔连绵不绝的是旅馆外面的鼎沸人声。
他看着百叶窗渗进的交织光影,出神喃喃道,“自此,天下无人不贵……”
“成何体统!”兄长面露厌恶,“成何体统!”
兄长枯老的胡须细微的抖动着,激动的情绪之下,却难掩几丝惶恐。
王石知道,大同社的所作所为,让兄长有些茫然了。
兄长提倡求实,厌恶士绅空谈天理,一贯只会务虚。
他虽然表面对大同社笔诛口伐,但实际上心中又不免赞同大同社的某些理念和做法,否则也养不出一个弃正道的儿子,否则也不会只在嘴上阻击儿子入学启明大学。
然而大同社的务实与兄长的务实当真是一回事吗?
兄长所求,乃是践行古圣人之道德,也就是去身体力行孔孟之道,实实在在地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改变自己、改变世人,而非只说不做。
大同社虽然也推崇并践行孔子之仁、孟子之重民,但又绝不止于此,孔孟之道仅是其爱民理念的源头之一,既非主体,更无独尊地位。
仅仅如此兄长或许也能接受,但偏偏大同社又否定了圣学之道德,只赞扬圣人,却不推崇圣人,只要求人去做人,不强求人去做君子。
大同社所谓人本思想,重视人之天性,保障天赋人权,鼓吹自由、平等、法治,似儒非儒,似法非法,似道非道,真不知从何处生发。
说来说去,兄长与大同社的矛盾便在“道德”二字。
兄长坚持,不追求道德,华夏便与蛮夷无异,即成禽兽之国。
大同社却认为人性自私,自私非罪,反而是一切进步的源头,道德只是个人的追求,而非国家的强制要求。
当然,大同社也并非完全放纵自私,其认为只需扼制有害的自私,无视无害的自私,并顺应发展化“自私”为“公私”,如此世人皆有公德,会发自内心地去追求道德。
兄长自然对所谓的“化自私为公私”嗤之以鼻,只觉得大同社如此作为,其治下百姓迟早道德沦丧。
“天下无人不贵!”兄长甚是气恼,“无论贩夫走卒,还是青皮无赖,皆成所谓‘少士’,皆与国朝士子相提并论,谁还要去读书!谁还要去做君子!”
他气得难以安坐,干脆站了起来,“大同社,用心何其歹毒!”
王石正想着劝说,门外却响起敲门声,一道男声隔着木门有些发闷,“两位先生,晚生接你们去见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