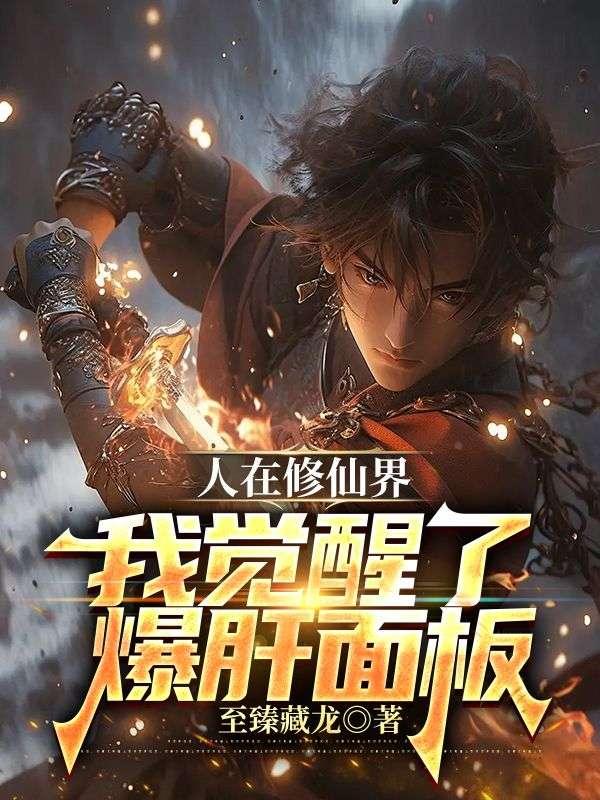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囚云阙 > 第 25 章(第3页)
第 25 章(第3页)
“然则,你重伤唐家嫡系,此事千真万确,恐难善了。为保你周全,免生事端,恐怕……要暂时委屈你了。”
他略一挥手,两名护卫应声上前,态度虽不算粗暴,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看守意味,一左一右,立于沈卿云身侧。
沈卿云没有丝毫反抗,甚至没有任何反应。
她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仿佛失了魂似的,手中紧紧攥着那封书信。
在真相与遗言的双重冲击下,她所有强撑的恨意与力气仿佛都被彻底抽空,只留下无边无际的茫然。
她究竟算什么呢?兜兜转转,挣扎反抗,甚至不惜双手染血,最终却连兄长的仇都未能亲手了结。
甚至,直至此刻,她才恍然惊觉,那将兄长推向死路的真正罪魁祸首,另有其人。
唐九霄。
她在心底反复咀嚼这个名字,齿间仿佛都漫上血腥气。
短短七日,像是过了一辈子。
彼时与他耳鬓厮磨,倾心相付时,她又何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这般怨毒地,近乎诅咒般地,一遍遍默念这个名字。
沈卿云最终被带离灵堂,软禁于一处偏僻院落,表面看守,实则却是密不透风的保护。
与此同时,唐家院落。
唐二白被悄无声息地送回。他身上多是皮肉伤,虽失血不少,看着骇人,但经随行大夫紧急处置,便已无大碍,只是脸色依旧苍白。
伤口甫一包扎妥当,甚至来不及换下那身血污狼藉的衣袍,便有侍从悄步而入,低声通传。
家主请他即刻过去。
唐二白听了,心头却没多少暖意。
自己身处囚牢,生死一线这段时日,这位父亲从未现身,甚至连一句关切的问询都未曾有过。
如今他刚脱险境,伤痕累累,对方却连片刻喘息之机都不愿给予。
他知道,父亲和母亲多年感情疏淡,仅仅维持着面上的相敬如宾。
再加之近年来,因崔家势大,屡屡试图插手蜀州事务,两家暗地里冲突摩擦不断,就连面上这点可怜的体面早已摇摇欲坠。
他早已不敢奢求父亲能待他如待唐九霄那般纵容和关注。
可人心,总归是肉长的。
偶尔,他也会难以抑制地生出那么点微末的期待。
期盼从那喜怒无常的父亲身上,得到那么一丁点,真正属于父子之间的温情。
而非永远冰冷的算计与权衡。
唐二白强忍着肩上剧痛,步履略显虚浮地穿过寂静的院落,终是停在那道低垂的,缀满珍珠的华美珠帘前。
然而,预想中的雷霆震怒并未降临。
率先闯入耳膜的,是棍棒重重击打在皮肉上的沉闷声响。
一声,又一声,节奏冷酷而稳定,间或夹杂着极力压抑却仍泄出的,破碎的闷哼。
那受刑之人显然已是进气少,出气多。
唐二白心下惊疑,掀帘绕过那面屏风。当看清地上那血肉模糊的身影时,他霎时间如坠冰窟,冷汗瞬间浸透了内衫。
是唐九霄。
那不是父亲最为看重,甚至时常纵容的儿子吗?
究竟犯了何等大错,竟招致如此酷烈的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