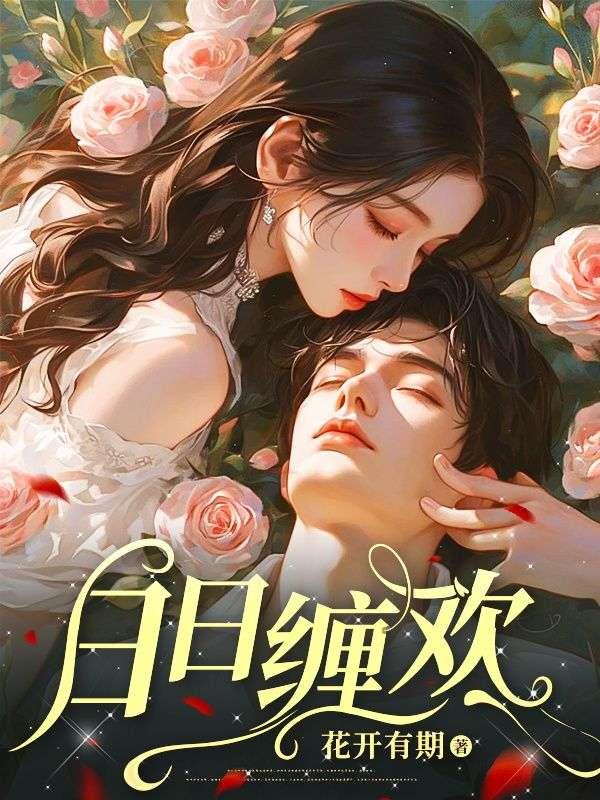宝书网>[暮光/凯厄斯同人]找到我 > 灰色地带(第2页)
灰色地带(第2页)
这时我才发现,床脚正卧着那卷白猫。
眉心一跳,我定定看着凯厄斯半晌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身体再次静止了,只有胸膛发出朦胧沉重的闷响。
“see,”他邪恶的笑了,“就算我用它威胁你,你也不听我的。”
沉黑的哑缎在我面上一掠而过,床又震了一震,下一瞬,掌心忽而降落一团温热,我静静地看着它,就像有人往我的掌心放了一颗长满绒毛,无比柔软的白色心脏。
咚——咚——咚。
确实有什么东西在我的手心跳动。是白猫的心,透过绵软的肚皮,一下一下落在我的皮肤。
凯厄斯走了。
赛琳,这是一场战争。
今天我就要把猫送走。
我撇了撇嘴,手举起来,把它恶劣地抖醒,把它抖得喵喵叫。它摇摇晃晃地抬脚,眼看它立马就要掉下来,手倏地放低,让它掉到柔软的白色被羽上,像塌倒的奶油。
“你找错了人,”我说,“但我会给你找个好地方。”
“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背上包出发了,我不愿意形容这种诡异的行踪为“躲避”或者“遮掩”,就好像我进行的是一种甜蜜的恐惧,一种戏码,这里不是上演这些戏码的地方。想着,我伏在转角的身姿挺直了,步伐变得平淡,手里的猫还在叫,我一把一把地给它顺毛,顺便借此捋直一些不必要的内心动荡。
我不惧怕任何一斗黑袍发现我,看到我,我对猫说。但它不再回应,找了个姿势窝好,我把它揣进了口袋。
已经到了8月,今天的天气并不明媚,少有的百分之三十的阴天,但现在还没有下雨,云在上空积了一层又一层,灰沉沉地压下来。阳光在云隙间游移,最终只在山谷的上空突破,裂开一道金光。
在公共巴士往坡上走的时候,那道金光又消失了,谷地陷入柔和的阴翳。
我上网查了几个宠物店,最优质的那些都聚在丽塔就读的大学附近。我先去了她的学校,推开她的教室,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画架摆的东一个西一个,地上散落着一些白纸,上面还有灰色的脚印。
学校进入暑假。一段潮湿闷热的狂欢。起码学校外面是这样。
我关了门正打算离开,走廊就传来一道声音,探身看去,一个单薄的背影在门边闪现,我捎上门向那边走去。
她穿着紫色的针织衫,下身是暗色的牛仔裤。她背对着我整理着掉在地上的画稿,弯曲的脊骨是一道流畅的弧线,裤边露出一点健康的小麦皮肤。此时正把地上的蜡笔和彩铅一股脑地扔进旧纸箱。
我轻轻地试探道:“丽塔?”
她倏地回头,弯曲的黑发掉落耳边,她笑了笑,“赛琳。”
这个名字噎住了我几秒,但我立马应了下来,“我好久没见到你了。”
她把最后几张纸扔进去,“我去了——”她顿了顿,“我去写生。跟一个小组去。”
我点点头。一时间无言。
她站起来,我终于看清她的脸,没有涂唇彩,没有画眉毛,而且,她剪了头发。
这时,口袋突然开始蠕动起来,发出一些细小的声音,我笑着冲她摆手,“你来。”
她放下纸箱,手在裤子侧边拍了几下,别了头发走近,我拉开口袋笑道,“伸手进去。”
她露出一点洁白的牙齿,用一个食指往里探。我看着她扬起眉毛瞪大眼,“一只猫?!”
“可以吗。”她询问我。
我笑着点头,她便把那只猫掏出来,眼睛弯弯地看猫在手上折腾。她静静地逗弄了一会儿,然后看向我:
“你想要来我的公寓喝一杯茶吗?”
“好啊。”
她玩猫有些入神,步子比我快,前方,平底蓝白帆布鞋轻巧地一起一落。我们的头顶是灰蒙蒙的天空,走过一个广场,有几个背包的人拾地而坐,丽塔和其中一个打了招呼,转头朝那人指了指我,我跟着他们一起笑,向他点头。
公寓藏在巷子里,被挤在两栋楼中间,黄褐色的墙面,但公寓的大门被漆成宁静又明媚的孔雀蓝,我忍不住摸了摸,丽塔笑道:“这是两年前我和房东的侄子一起漆的,我负责调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