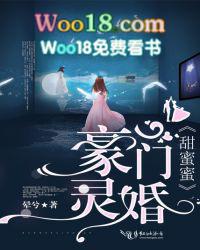宝书网>状元郎 > 第三二七章 洗澡(第2页)
第三二七章 洗澡(第2页)
他立即召集当地渔户、老舵工十余人,在净慈寺偏殿设坛研讨。众人对照地图,纷纷惊叹:“原来往琉球不必绕行福建外洋,取黑潮支流北上,七日可达!”“此处‘龟屿’确有淡水泉眼,可作歇脚!”“冬季东北风起时,当走内海槽道,避巨浪!”
林昭命人誊抄副本三份:一份呈送御览,一份交工部造船司改进海舶设计,另一份则秘密送往登州水师,加强海防预警。
正当诸事渐入正轨,忽接急报:秀州海盐县爆发民变,数千饥民围攻县衙,烧毁漕仓,声称“拒修海港,还我河运”。更有流言四起,说“林状元欲引倭人入寇,卖国求荣”。
林昭当即率随从兼程赶往。途中遇暴雨倾盆,道路泥泞难行。至海盐城外十里,忽见前方火光冲天,喊杀声隐隐传来。
“不好!”林昭催马疾驰。赶到城下,只见城门紧闭,守军慌乱不堪。知县满脸焦灼迎出:“林大人,贼众已破东栅,眼看就要攻城!他们打着‘诛国贼林昭’的旗号,说您要掘断龙脉,引海水倒灌良田!”
林昭翻身下马,沉声道:“开城门。”
“不可!”众人惊呼。
“不开城门,民心愈惧。我若避而不见,反坐实谣言。”他整了整衣冠,“备轿,我去见他们。”
一刻钟后,一顶青呢小轿缓缓穿过吊桥,停在东门外。林昭步行上前,面对黑压压的人群,朗声道:“我是林昭,你们口中的‘国贼’。今日不带兵卒,只身前来,愿听尔等控诉。”
人群骚动。有人怒吼:“你毁祖宗规矩,通倭卖国!”
也有老农哭诉:“我家田地靠运河灌溉,若改海运,河道荒废,我们吃什么?”
林昭静静听着,忽然跪地,叩首三下。
全场寂静。
“各位父老,”他声音低沉却清晰,“我林昭之父,曾因主张海运被罢官流放,家破人亡。我母,东瀛女子,却为大宋卧底破敌,终生不敢言出身。我之所以坚持此策,并非为名利,只为不让他们的牺牲白费!”
他取出《扶桑水道图》副本,高高举起:“此图来自我母亲遗物,记录千年航海智慧。它不是为了侵略谁,而是为了让我们的船只不再迷航,让渔民能平安归来,让灾年时南方粮食可速抵北方救饥!”
他又拿出户部最新奏报:“去年黄河决口,河北饿殍遍野。若那时已有海运,三十万石米粮十日可达天津港,何至于万人易子而食?”
人群中渐渐有人低头啜泣。一位老渔夫颤声道:“我家三个儿子都葬身风涛……若是有了这张图,或许……或许还能活着回来……”
林昭起身,环视众人:“我不强迫任何人。但请给我一年时间。若一年后,海运不能让你们多赚一文钱、少吃一顿苦,我自愿辞官谢罪,永不提此议!”
沉默良久,一个少年走出人群,扔掉手中火把:“我信林大人。我爹就是饿死的,我不想再等河运慢慢拖粮了。”
紧接着,第二支火把熄灭,第三支……最终,上千支火炬逐一熄灭。人群缓缓散去,留下一句低语在风中飘荡:“状元郎……是真的想为我们好啊。”
事后查明,此次民变乃前户部郎中刘元吉幕后操纵。此人系高俅旧党,私通辽国残部,妄图借民心动荡阻止海运,保住自身走私利益。林昭下令将其逮捕,押解回京受审。
一个月后,首艘试验海船“安澜号”自杭州启航,载粮五千石,驶往登州。林昭亲自登船督航。出港那日,沿岸百姓夹道相送,鞭炮齐鸣。有老人含泪跪拜:“愿海神护佑,送粮船一路平安。”
航行第七日,遭遇狂风巨浪。船体剧烈摇晃,桅杆断裂,水手惊恐万状。危急时刻,林昭取出母亲的地图,对照星象与洋流,果断下令转向东南,驶入一处隐秘海湾避风。此湾正位于图中标注的“龟屿”附近,果然风平浪静。
三日后风息,续航登州,全程仅耗十二日,较河运快逾半月。消息传回汴京,举朝震动。
皇帝亲书“经世济民”匾额赐予林昭,并下诏:“自今以往,凡沿海要港,皆设市舶分司,专理海运;擢林昭为户部右侍郎,总领新漕政。”
庆功宴上,同僚举杯恭贺,林昭却悄然离席,独自登上皇城角楼。夜空繁星点点,宛如母亲当年讲述故乡传说时眼中闪烁的光。
“娘,您看到了吗?海,真的活了。”
一阵清风吹过,仿佛有人轻轻回应。
数年后,大宋海运体系初具规模,南粮北运效率提升三倍,沿海兴起数十座贸易港口,倭商、高丽使、波斯贾人纷至沓来。林昭主持编纂的《海道图志》正式刊行,成为航海者必携之宝典。
而在杭州净慈寺后山,一座新坟静静伫立,碑文简洁:
**大宋贞烈夫人陈氏千代之墓**
每年清明,必有一人白衣素服前来祭扫。他不焚纸钱,只献一束樱花??那是母亲故乡的花。
某年春深,一位白发老道悄然出现在寺中,望着墓碑良久,微笑离去,只留下半阙题壁诗:
>“一身清誉归天地,
>两袖风雷动古今。
>莫道书生无胆气,
>翻手云雨定乾坤。”
自此,再无人见过此人。唯有孩童传说,每逢海雾弥漫之夜,可见一叶扁舟驶于钱塘江口,舟上似有一青衫书生执卷而立,身后隐约有紫袍老者、东瀛妇人含笑相随。
松风阵阵,涛声不绝。大宋的船帆,正乘风破浪,驶向未知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