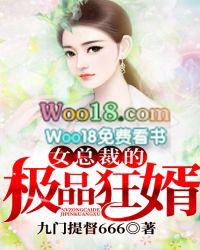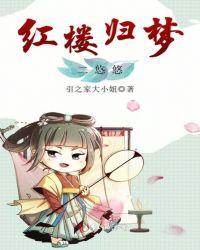宝书网>状元郎 > 第三一六章 师徒相会(第3页)
第三一六章 师徒相会(第3页)
首先,他命《女子日报》连续刊登《逃亡日记》系列,记录被捕女师在狱中遭遇:有人被逼跪碎瓷片,有人遭酷刑逼供“幕后主使”,有人写下血书“我读诗书,何罪之有?”文字凄厉,震动人心。
其次,他联合浙江、江苏两省士绅联名上书,要求“依法审判,不得滥捕无辜”,并邀请在京的三位女学士代表赴刑部请愿,强调“教育乃民权,非地方可擅断”。
最关键的一招,是他亲自修书一封,托人秘密送往西北边关??交予正在督军抗蒙的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王守仁。
信中只写一句:“昔阳明先生讲‘致良知’,可知今日天下最大之恶,乃是阻止他人知晓真理?”
三日后,边关回音传来。
王守仁在军中召集将领,当众宣读苏录来信,慨然道:“若连女子求知皆不容,何谈天下太平?我虽远在塞北,亦知江南灯火未灭。此非小事,乃文明存续之机!”随即具折上奏,直言“封闭女学,伤仁政之本,损朝廷威信”,并以辞官相胁。
朝野哗然。
一位手握重兵、德高望重的封疆大吏,竟为女子教育不惜挂印而去,谁敢承担后果?
皇帝终于震怒。一道严旨飞驰天下:“各省擅自封闭女子学堂者,巡按御史立即弹劾;已捕之人,限三日内释放;焚毁教材者,照价赔偿,另罚俸半年。朕言至此,若有再犯,视同谋逆!”
圣旨所至,江西巡抚惶恐谢罪,被迫开释全部女师。其他省份纷纷收敛,风波暂平。
苏录站在孤山书院门前,望着重新升起的蓝旗,心中却没有丝毫轻松。
他知道,这场战争的本质,早已超越男女之别。它是蒙昧与启蒙之争,是封闭与开放之斗,是权力垄断与知识共享之间的生死较量。
而他所做的,不过是点燃了一盏灯。
多年后,有人问苏录:“您一生最骄傲的事是什么?”
他没有回答科举高中,也没有提官居二品,只是轻声道:“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小女孩,拿着毛笔,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是刻进石头里。那一刻我明白??只要还有人愿意写字,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彻底黑暗。”
时光流转,春风又绿江南岸。
那年秋天,“女子科举附加试”迎来首届放榜。百余名“闺秀才”身着蓝裙立于贡院前,阳光洒在她们脸上,映出坚毅与希望。林晚照再次夺魁,被任命为绍兴府文书参事,专管水利账目审计。
她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会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你们忘记我们是‘女子’,只记得我们是‘人’。”
台下掌声如雷。
苏录站在人群之后,默默注视着这一切。他的头发已全白,背也微微佝偻,可眼神依旧清澈如初。
忽然,一个小男孩挣脱母亲的手,跑到林晚照面前,仰头问道:“姐姐,我妹妹以后也能像你一样当官吗?”
林晚照蹲下身,认真地说:“不只是当官。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只要她敢想,敢学,敢写下一个字。”
男孩用力点头,转身跑回人群,大声宣布:“娘!我要教妹妹写字!”
众人哄笑,笑声中带着暖意。
苏录闭上眼,任春风拂过面庞。
他知道,那盏油灯仍在燃烧。
而且,正越烧越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