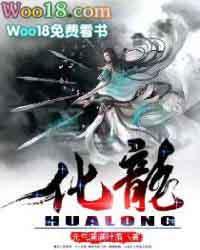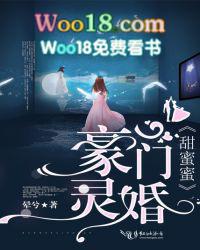宝书网>状元郎 > 第三一五章 王守仁的奇幻漂流(第1页)
第三一五章 王守仁的奇幻漂流(第1页)
手下有人提醒千户道:“大人,刘公公要的人,总得活见人、死见尸吧。”
“他跳的是钱塘江,这会儿都冲到东海龙宫里去了!”千户没好气道:“那你就留下来慢慢搜吧,找不到人不许回去。”
“别别,当小。。。
晨光如薄纱覆地,苏录独坐窗前,手中那页白纸在风中微微颤动。油灯之象,是绝境,也是希望??他深知,敌人不会因一次败退而收手,他们只是潜入更深的暗处,等待下一个裂隙。而这盏将熄之灯,正是他与万千女子命运的写照:微弱,却未灭。
他将纸收入袖中,起身整衣,缓步出门。今日乃“女学士”授衔后首场讲学会,地点设于西湖畔孤山书院旧址。此地原为南宋理学讲坛,百年沉寂,今朝重开,竟由一群女子登台论道,实为前所未有之举。消息传开,四方云集,不仅有本地士绅、学子,更有远自徽州、金陵而来的文人名士,皆欲亲睹“女子登堂”的奇景。
苏录行至山门,见青石阶上已排起长队。蓝裙素服者列队而立,神情肃穆,眼中却燃着不屈的光。她们中有农妇裹布巾而来,有渔家女赤足踏露而至,亦有老妪扶杖缓行,一步一叩心志。书院门前高悬横幅,墨迹遒劲:“学问无别男女,明理即为圣徒。”
忽闻身后马蹄声急,一辆朱轮华盖马车疾驰而来,尘土飞扬。车帘掀开,走出一位锦袍官员,面白无须,手持象牙笏板,正是礼部派来“监察试点”的给事中陈文昭。此人素以守礼自居,曾上疏称“妇人识字,乱伦之始”,如今奉旨前来,名义上是“观礼指导”,实则人人皆知其意在挑刺。
苏录迎上前去,拱手作礼:“陈大人亲临,实乃我等荣幸。”
陈文昭冷眼扫过入场诸女,鼻中轻哼:“苏大人好大的胆子,竟敢让此等身份之人登圣贤之堂。你可知孔夫子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下官亦知。”苏录平静答道,“然夫子未曾言女子不可读书。若因一句断章取义之语,便锁住天下半数人口之智,岂非误读圣训?且《礼记》有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何曾限定性别?”
陈文昭脸色微变,正欲反驳,忽听钟声三响,讲学会正式开始。
主讲席上,第一位登台的是那位六旬老妪,名唤沈氏,人称“沈婆婆”。她拄拐立于台前,声如洪钟:“老身幼时偷听私塾三年,记下《论语》半部。父亲发现后,烧我笔记,罚我跪祠堂一日。他说女子读书,会妨兄弟仕途。可如今,我三个孙女皆入学堂,最小的已能背《孟子》全文。请问陈大人??”她目光直射台下,“是我妨了谁,还是谁妨了我?”
全场寂静,继而爆发出雷鸣掌声。陈文昭面皮涨紫,拂袖欲走,却被周延儒亲率两名侍卫拦住去路。
“陈大人何必急着走?”周延儒缓步登台,声音不高,却压下全场喧哗,“您既来监察,便该听完全程。否则,如何向朝廷禀报真实情形?”
苏录悄然退至角落,只见人群中一名黑衣男子迅速转身离去。他心头一紧,认出那人正是半月前曾在白云庵附近出现的信使模样的人物。他立刻命书童尾随,自己则留心观察会场动静。
果然,不到半个时辰,外头传来骚动。一名衙役匆匆奔入,在苏录耳边低语:“少爷,城南火药库突发大火,巡检司怀疑有人纵火!更糟的是……贡院外墙被人泼满红漆,写着八个大字??‘妖女惑世,天怒人怨’!”
苏录心中雪亮:这是连环布局。先以讲学会制造轰动,再借“天灾人祸”渲染恐慌,最后嫁祸女子学堂“触怒上苍”,从而逼朝廷废除特科。手段狠辣,节奏精准,必是老对手卷土重来。
他立即赶往贡院。沿途所见,民心浮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人信誓旦旦说昨夜看见“蓝裙女子夜祭火神”,更有巫婆跳傩称“阴气冲天,需斩首七人方可平息”。
贡院墙上血字触目惊心,红漆未干,腥气扑鼻。苏录伸手轻触,发觉并非鲜血,而是混合朱砂与猪血调制而成,极似祭祀用物。他猛然想起,绍兴一带民间确有“血书告天”之俗,常用于重大控诉或诅咒。若此事被曲解为“百姓共愤”,后果不堪设想。
当晚,他在梅园密召心腹幕僚,汇总线索:
其一,火药库守卒供述,失火前曾见一名“戴帷帽的妇人”送茶水,事后消失无踪;
其二,泼漆之人作案时骑一匹枣红马,马蹄铁印呈罕见倒“品”字形,已在城西马市查到同款印记,买主登记名为“李福”,系盐运使府账房仆役;
其三,那位神秘黑衣人经追踪,入住城北悦来客栈,今晨已乘船北上,船上悬挂“苏州织造局”旗号。
“又是刑部御史团的人。”苏录咬牙道,“他们这次不只是想毁制度,还想掀起民变。”
周延儒沉吟片刻,忽问:“可有证据指向幕后主使?”
“有。”苏录取出一封密信,“今日清晨,一位匿名线人送来这份名单,记录了近三个月内十余位地方官员收受盐运使贿赂的明细,其中赫然包括陈文昭之弟??时任嘉兴盐税提举。”
周延儒双眼骤亮:“好!这就够了。”
次日清晨,《钱塘时报》头版刊发苏录署名文章《谁在纵火?》,全文以冷静笔调还原事件经过,指出所谓“妖女惑世”纯属构陷,并附上火药库监控图、马蹄印拓片及部分受贿账册影印件。文章末尾质问:“当真正的罪犯躲在幕后放火,却让无辜女子背负骂名时,我们究竟是在护道统,还是在助奸邪?”
舆论再度翻转。百姓开始质疑:为何偏偏在女子考试之后发生怪事?为何每次改革推进,总有“天谴”降临?民间画师甚至绘出讽刺年画:一群官老爷围炉烤火,脚下踩着书本与女童鞋履,头顶乌云密布,雷电劈向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