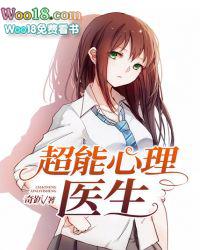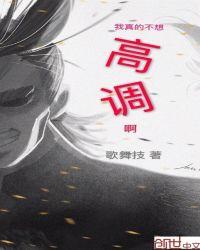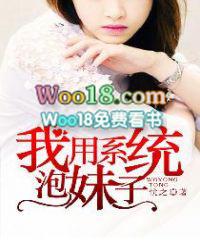宝书网>俗仙 > 363我等狐族乃是良善之民(第1页)
363我等狐族乃是良善之民(第1页)
大日魔经由十万八千问魔禅,有三生幻世劫,修的是根本魔心,大灭魔经却修的是皮骨,正修为佛,逆修为魔,乱修为妖,诸般法力各生冲撞,故而须得舍法为外物,所有法术都尽显化为法宝姿态。
比如八苦浮屠云车,。。。
春雷在天际滚过,青崖山的晨雾尚未散尽,井边已围满了孩童。他们手中捧着各色纸灯,有的画着笑脸,有的写着名字,还有的只是胡乱涂了一团暖黄??那是他们心中“光”的模样。小女孩蹲在最前头,如今她的发间已夹杂银丝,但动作依旧轻柔,像当年那个许愿的孩子般小心翼翼地将一盏小灯放入水中。
灯浮于暗河之上,随波缓缓前行,仿佛载着整座人间的愿望向地心深处驶去。水面微漾,倒映出天空裂开的一道缝隙,九光环阵虽已隐去,却并未消失,而是沉入云层之下,如呼吸般起伏不定。每当有人真心铭记、诚心悔悟,那环阵便会在无形中亮起一丝弧线,像是天地之间悄然缝合的针脚。
远处学堂里传来诵读声,稚嫩而坚定:“我愿记得父亲教我的第一句诗,母亲临终前握紧我的手,邻居阿婆每日为孤老送饭的脚步……”这是孩子们每日晨课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一句必须背诵的话。老师说,记不住别的不要紧,只要记得“记得”本身,就够了。
就在这时,一阵马蹄踏破宁静。
一骑快马自官道疾驰而来,尘土飞扬,马背上是一名年轻驿卒,肩披褪色蓝袍,胸前绣着“急递”二字。他翻身下马,气喘吁吁地奔向学堂门口的老槐树,从怀中取出一封泥封文书,郑重贴于公告板上。围观者纷纷凑近,只见上面朱笔批注:“奉旨昭告天下:《省亲令》升格为国典,凡不归乡祭祖者,三代之内不得应试入仕。”
人群中有人低语:“这规矩,竟是从一个渔夫嘴里传出来的?”
“可不是。”一位拄拐的老妪摇头,“听说那老渔夫临死前念叨的,不过是一句‘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件好事’。谁能想到,一句话竟能撬动江山社稷?”
话音未落,忽见公告板旁的桃树无风自动,一片玉叶轻轻震颤,竟自行脱落,飘至文书之上,如印章般覆盖其首。刹那间,墨迹泛金,字字生辉,仿佛有千百双眼睛在背后凝视着这一纸政令。
与此同时,在西漠废墟,“守剑人”正跪坐在阵基边缘,手持铁剑划地为文。他年岁渐长,双手布满老茧,每一笔都沉重如碑刻。今日所书,非誓言,亦非训诫,而是一份名单??三百七十二个名字,皆是这些年在他庇护下长大成人的孤儿之名。
“你们不是无根之人。”他一边写一边喃喃,“你们的名字,从此刻起,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
话音刚落,沙地忽然泛起涟漪,那些名字竟逐个下沉,没入地下,如同种子归土。片刻后,阵心铁剑嗡鸣一声,锈迹剥落,露出内里寒光流转的刃身。一道清音自剑尖迸发,直冲云霄,与高空中的九光环遥相呼应。
而在北冥冰原第三渊,那片悬浮的桃瓣猛然一颤,从中分裂出第二片,轻盈飞旋,越过万里雪原,落向南方一座荒庙。
庙中无人,唯有一尊残破木像端坐神龛,脸上漆皮剥落,依稀可辨是陈三七年轻时的模样。香炉早已干涸,蛛网横织,唯有角落里堆着厚厚一叠纸条,全是各地旅人路过时留下的心事。有人写:“我偷过别人的粮食,但我后来还了十倍。”有人写:“我曾背弃朋友,如今每夜梦见他站在雨中等我道歉。”
桃瓣落下之时,整座庙宇轻轻一震,木像眼中竟渗出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最上方那张纸条上。纸条瞬间燃烧,化作灰烬升腾,形成一个模糊人影,低声说道:“够了……你们都够了。”
那声音温柔得像春风拂面,却又沉重如山岳倾覆。
同一时刻,东海海底石台再度浮现,碑文新增一段,字迹苍劲有力,似由无数手掌共同推动而成:
>“大道不在高处,而在低头看见蝼蚁搬家的那一刻;
>真理不在经卷,而在老人摔倒时你犹豫是否上前扶起的那一秒。
>成仙不易,做人更难。
>可若人人肯在黑暗中多点一盏灯,
>这世间,便永不沦陷。”
老渔夫的孙子如今已是中年汉子,每年仍驾船前来诵读碑文。今日读罢,他忽然觉得胸口发热,伸手探入怀中,掏出一枚贝壳,里面藏着一缕青蓝色的丝线??那是祖父临终前交给他的“信物”。
丝线一触空气,立刻舒展延展,竟自行缠绕成一只微型灯笼,悬于掌心微微发光。他怔住,耳边响起祖父的声音:“这不是法器,也不是神通,这是‘愿力’的凭证。只要你还记得他说过的那句话,它就不会熄灭。”
他跪倒在船头,对着大海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千里之外的皇宫旧址,曾经的冷宫院墙早已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简朴祠堂,供奉着那位焚书明志的贵妃灵位。每逢清明,总有陌生女子前来献花,不言姓名,只留下一首手抄的《守山谣》。今晨,一名盲女缓步走入,怀抱古琴,席地而坐,指尖轻拨,琴音清越,唱的是:
>“山不会说话,水也不会回答,
>可人心若冷,万物皆冬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