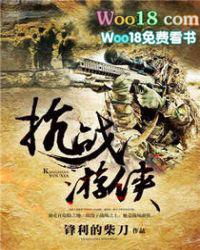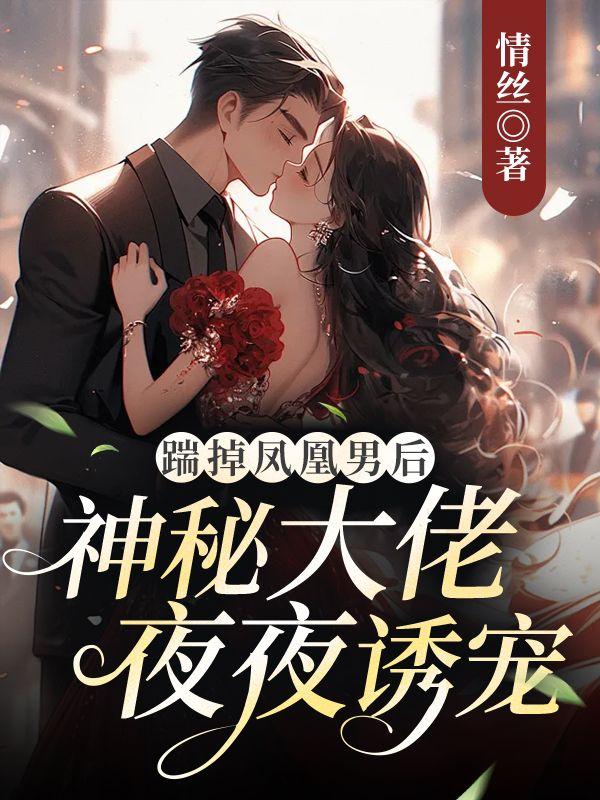宝书网>俗仙 > 362入魔门我为魔主入沙门我为世尊(第1页)
362入魔门我为魔主入沙门我为世尊(第1页)
青丘狐族虽然天赋寻常,已经多年未出过大修,但作为仙宠却甚受欢迎,许多狐族子弟都在各处仙门的二三代弟子身边,或者做小妾,或者做小厮,或者做纯宠,或者表演才艺,或者只是玩物,遍布极广。
故而这位万年。。。
夜深了,青崖山下的灯火一盏接一盏熄灭。那口古井遗址旁的投币箱微微震动了一下,硬币悄然翻转,正面朝上,映着月光泛出温润铜色。井底水影轻轻晃动,仿佛有谁在深处眨了眨眼。
小女孩并不知道,她许愿的那一刻,九块玉髓同时震颤。它们早已不是实体,而是化作大地的记忆脉络,藏于江河之源、埋于群山脊梁、沉于人心最柔软处。那一声“好”,并非来自风,也不是幻听??它是千万个曾低头赶路却仍扶起跌倒孩童的手,是无数个在黑暗中选择不说谎的唇,是那些明知无果仍种下一棵树的人心中共同响起的回音。
而此时,在遥远的北冥冰原第三渊,风雪再起。不是暴虐的寒潮,而是一种温柔的涌动,如同大地呼吸。祭坛上的裂缝已缓缓闭合,唯有一片桃瓣静静躺在冰面,晶莹剔透,内里封存着一抹微弱却不灭的意识。
小白走了,但它没有消失。它的魂魄散入天地,成为“忆途”的引路人。每逢清明雨落、霜降晨雾,总有旅人声称看见一只白狐穿行于荒野,身后跟着模糊的人影:有的背着药箱,有的提着灯笼,有的怀抱书卷。他们不言不语,只默默行走,所过之处,枯草返青,断碑自立,被遗忘的小径重新浮现。
有人追随其后,走了七日七夜,终于抵达一座无人知晓的村落。村口石碑刻着三个字:“归心里”。村民见他到来,并不惊讶,只是递来一碗清水,说:“你迟到了二十年。”
那人猛然记起??他曾在此地答应母亲,每年春分回家扫墓。可后来功成名就,便将此事抛诸脑后。如今父母双亡,坟茔荒芜,连名字都快从族谱上抹去。
他跪倒在祠堂前痛哭流涕,当晚写下《还亲书》三十六篇,详述自己如何背弃亲情、追逐虚名。次日清晨,整本书化为灰烬升空,随风洒向四方。自此以后,天下兴起“省亲令”,官府明文规定:凡在外为官经商者,每三年必归乡祭祖,违者削籍罢职。
与此同时,东海浪底传来异响。渔民驾船经过某片常年平静的海域时,忽觉船身下沉,锚链绷紧如弓弦。潜入水下查看,竟发现海底升起一座石台,台上立碑,碑文正是当年陈三七亲手所书的《守山誓》全文。更奇的是,每当月圆之夜,碑底便会浮现出新的段落,似由无形之手续写而成。
一位老渔夫每日驾小舟前来诵读,风雨无阻。十年后他寿终正寝,临死前对子孙道:“我非贤人,亦未修行,但我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件好事,死后就少一道悔恨。’”
话音落下,海面波澜骤起,石碑缓缓沉没,却在最后一瞬射出一道金光,直指西漠方向。
那里,曾经的祭城废墟之上,沙尘退去,露出一片巨大的圆形阵基,与高空中的九光环遥相呼应。阵心位置,赫然插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剑??正是当年陈三七初入修行界时,用以斩断邪修阴谋的第一柄兵器。此剑本应毁于战火,却不知何时被人悄悄带回,深埋于此,直至今日因愿力复苏而重现人间。
一名流浪少年偶然路过,伸手触碰剑柄。刹那间,脑海中涌入无数画面:一个年轻人跪在井边发誓,一群百姓冒死掩护逃难的记述者,一位盲眼老人临终前将《山语录》交到孩子手中……
他浑身颤抖,泪流满面,喃喃道:“我不是什么天选之人……可我也想守住点什么。”
于是他拔剑起身,不再漂泊。他在废墟上搭起茅屋,收留失孤儿童,教他们识字、耕田、讲道理。几年下来,竟形成一个小聚落。人们称他为“守剑人”,但他总摇头:“我不守剑,我守的是那些没人记得的故事。”
这些事,看似零散,实则如蛛丝牵引,彼此相连。正如《玄微真解》补全后的最后一章所言:“大道非独行,众生共织网。一人念起,万缘俱动;一愿不灭,百劫可渡。”
这一日,江南梅雨绵延。书院中,那位掌心有桃形胎记的少年已成长为学者,主持编纂《俗世志注疏》。他在序言中写道:“仙不在云端,而在巷陌之间。所谓‘俗仙’,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不平凡的善良。”
正当他执笔至此,窗外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开乌云,照亮整座庭院。惊见院中桃树无风自动,八片玉叶齐齐震颤,其中一片忽然脱落,飘至案前,轻轻覆盖在他写下的“善良”二字上。
那一瞬,他仿佛听见陈三七的声音,低而清晰:
“最难的不是牺牲,是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依然愿意相信光。”
与此同时,皇宫之内,贵妃早已不在。当年她因直言触怒帝王,被贬冷宫,三年后病逝。临终前,她将多年抄写的《山语录》投入火盆,口中轻唱《守山谣》片段。火焰腾起之时,灰烬竟未落地,反而逆飞而上,穿过屋顶,融入夜空,化作一颗新星,悬于北斗之侧。
民间传说,那是“心灯星”,专照迷途之人。尤其战乱年代,常有士兵在荒野抬头望见此星光亮,便毅然放下屠刀,返乡务农。史载:“永和七年,边军哗变,主帅欲屠城立威。当夜天现异星,士卒皆泣,曰:‘娘在家等我。’遂集体归降。”
岁月流转,又三十年过去。
青崖山脚下的点灯祭依旧年年举行,但参与者已不限本地村民。四面八方的人跋山涉水而来,只为在山顶点燃一盏灯,寄托一段未竟之情、一句迟到的道歉、一份藏了半生的感激。
这一年,来了个身穿黑袍的老者。他步履蹒跚,脸上覆着面具,只露出一双浑浊却深邃的眼睛。他不说话,也不与其他香客交流,独自捧着一盏油灯,缓慢攀登。
中途风雨突至,山路泥泞湿滑。几名年轻男子讥笑他:“这般年纪还来受罪?不如回去歇着。”
老者只是低头前行,任雨水打湿衣袍。
待他终于登上山顶,已是深夜。众人见他取出灯芯,竟是用一缕白发搓成。点燃之后,火焰呈淡金色,竟能穿透浓雾,直射苍穹。
就在那一刻,天空再次显现九光环阵,古井虚影重现,藤蔓摇曳,布袋微启。八块玉髓光芒大盛,第九块依旧空缺。
老者仰头凝视,忽然双膝跪地,摘下面具。众人惊骇??此人竟是当年下令焚毁《守山经》、镇压记述者的首辅大臣!他曾权倾朝野,推行“去妄令”,严禁一切与“守山”相关的言论,甚至亲自监斩七十二名传书者。
此刻的他,满脸皱纹纵横如沟壑,眼中却涌出滚烫泪水。
“我……也曾是个读书人。”他声音嘶哑,“年轻时也梦想济世安民。可后来,怕了。怕民心浮动,怕秩序崩塌,怕控制不住这滔滔民意……所以我烧书、杀人、封口,以为这样就能保住太平。”
他颤抖着手,从怀中掏出一本残破小册,封面焦黑,依稀可见“山语”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