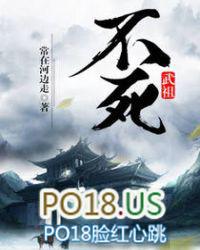宝书网>魏晋不服周 > 第215章 秘不发丧(第1页)
第215章 秘不发丧(第1页)
洛阳宫,云龙门城楼签押房,石守信正在编写排班表,同时对左卫兵马中的中高级军官,进行“背景审查”。
是谁家的人,老家在哪里,家中还有什么人,都被查得底朝天。
不得不说,这几天收获非常大。
。。。
风起玉门,黄沙漫卷。敦煌城外的荒原上,一队少年正围坐在干涸的河床边,用炭条在陶片上临摹《双碑定法》第三章:“凡征调民力、征收赋税,须公示七日,由三老五更联署方可施行。”他们身后插着一面褪色的布旗,上书“律童习坛”四字,是去年共审庭批准设立的民间讲学点之一。这些孩子多为牧民与戍卒之子,白日放羊耕田,夜晚聚此读书。有人不识字,便靠口传心记;有人手冻裂了,仍坚持一笔一划写下自己听过的判例。
阿禾远远望着,未上前打扰。她如今已不再频繁露面于公议坛前,而是将更多时间留给培养新一代律佐。启明说她像一棵老胡杨,根扎得越深,枝叶反而越向远处伸展。乌仁娜则笑言:“你这是把命刻进石头里了,风吹不走,沙埋不住。”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急促的驼铃声。一名身披羊皮斗篷的少女飞身下驼,手中紧握一封火漆封印的文书??来自西域都护府的加急军报:龟兹王庭突发政变,亲北魏派贵族联合焉耆兵马夜袭宫城,现任国王仓皇出逃至高昌边境,请求敦煌方面依“丝路互保盟约”提供庇护,并协助调查幕后黑手。
阿禾眉头微蹙。龟兹素来亲汉,且曾公开支持共审制度,在其境内已有三座城镇试行简化版《双碑定法》。若此番被颠覆,不仅河西外交格局动摇,更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使其他观望中的城邦退缩自保。
“这不是内乱,是清算。”启明翻阅密报附件时冷声道,“你看这份名单,被捕的七名大臣中,竟有五人曾在敦煌参加过‘律政研修班’,其中两人还是《龟兹市令》的起草者。他们不是得罪权贵,是触犯了旧秩序的根本。”
乌仁娜冷笑:“所以崔琰虽倒,他的影子仍在万里之外杀人。”
阿禾沉默良久,终起身走向祠堂后的议事窑洞。那里挂着一幅手绘舆图,红线串联起十三座共议分坛,蓝点标注历年冤案平反地,红叉则代表已被清除的贪官据点。她在龟兹位置钉下一枚铜钉,又从匣中取出一封旧信??正是陆修文那日派人送来的亲笔函副本。信纸边缘已泛黄,但“若有伪造,天地共殛”八字仍如刀刻般清晰。
“他没说谎。”阿禾低语,“但也未全说实话。陆修文反对妇人参政,却不愿见血流成河。可有些人,既不要理,也不要命,只要权柄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次日清晨,阿禾召集跨族评议会紧急会议。粟特商会长老、吐谷浑使者、汉羌混居村代表悉数到场。议题明确:是否援救龟兹流亡政权?若援,以何名义、何种方式?
争议迅速爆发。商人主张谨慎:“丝路安稳第一,贸然介入恐招北魏报复,商路断绝,万民受困。”军屯校尉则拍案而起:“高昌已屯兵两万,虎视敦煌!若坐视龟兹沦陷,下一个就是我们!”而寺院住持沉吟道:“佛门劝和,不宜兴兵,然正义不可弃。”
阿禾静听各方陈词,直至黄昏。最后,她取出一块新烧制的陶板,上刻一行小字:“昔年我跪于县衙阶下,无人肯听我说话。今日有人千里奔来求一声公道,我们岂能闭门?”她将陶板置于案首,“此案不涉出兵,只问一事:当弱者呼救,我们是否还相信法律能跨越沙漠?”
全场寂然。
投票开始。五百名陪审员逐一上前,在黑白石子间选择立场。黑石为否,白石为是。最终,白石堆高出半尺。决议通过:敦煌将以“共审庭特别观察团”名义派遣使节团赴高昌边境,护送龟兹国王至安全地带,并启动跨境司法调查程序,查明政变资金来源及外部干预证据。
七日后,使节团出发。领队并非官员,而是三位平民身份的律佐??盲童阿乙、粟特女商苏玛、退役戍卒李十七。他们携带着最新修订的《国际讼约草案》,首次尝试将“民众自治”原则推向域外。临行前,阿禾亲自为三人系上象征中立的白麻绶带,并赠予一只密封陶罐,内藏双碑拓片与历年重大判决汇编。“若你们被扣留,”她说,“就把这罐子砸碎,让风把文字吹遍西域。”
与此同时,建康方面再起波澜。新帝虽颁诏承认敦煌试点,但朝中保守势力暗流汹涌。太常卿联名上奏,称“双碑悖礼,蛊惑民心”,请求派遣“礼法官”入驻敦煌,督导“复归正统”。更有御史弹劾李承徽巡察报告“夸大异俗,贬损纲常”,致其被调离实权职位,贬为闲散顾问。
消息传回,赵元礼怒极反笑:“他们怕的不是我们违法,是我们太守法。百姓一旦学会用规则对抗强权,谁还肯低头磕头?”
阿禾却神色平静。她知道,真正的斗争不在朝堂争辩,而在人心取舍。于是她下令开启“千村讲律计划”:选拔百名优秀律佐,深入边远村落,以方言说唱、皮影演案、陶片问答等形式普及法律常识。每到一处,便在当地立一小碑,刻一句最贴近民生的律文。有村无匠人,孩童便用泥巴塑字;有寨缺陶土,牧民就在岩壁上凿出浅痕。
某日在疏勒故道旁的小村,一位老妪颤巍巍递上自己写的诉状:二十年前,官府强征其夫修渠,途中累死,尸骨未归。当年无人敢问,如今她听说“迟来的正义也可追索”,便拄拐步行三日而来。
阿禾亲自受理此案。经核查档案与幸存役夫证言,确认属实。共审庭裁定:由现役水利主管机关出具正式道歉文书,镌刻石碑立于渠首,并从公共救济基金中拨付抚恤金三十缗。判决公布当日,老人跪地嚎啕:“我活到七十岁,第一次听见官家说对不起。”
此事传开,四方震动。越来越多尘封旧案被重新提起。有人告发先父因言获罪,家族三代不得科举;有人申诉祖母田产被豪族巧取豪夺,族谱尽毁。阿禾一一准许立案,但设下严规:必须提供至少两项可信证据,禁止煽动仇恨,裁决结果不得追溯死刑或株连。
她常说:“我们要洗清过去的冤屈,而不是制造新的敌人。”
冬去春来,又是一载。龟兹使节团传来捷报:经三个月交涉与证据交换,高昌迫于舆论压力释放国王,并承诺举行全民评议决定国策走向。更令人振奋的是,当地青年自发组织“陶板会”,模仿敦煌模式收集民意,甚至将《双碑定法》译成龟兹文,在集市公开宣讲。
然而胜利背后,阴影从未消散。某夜,阿禾正在灯下整理案卷,忽闻院外响动。巡夜的乌仁娜带回一名重伤男子,浑身箭伤,怀中死死抱着一只漆盒。他是前往凉州传递密信的信使,途中遭伏击,同伴皆亡。盒中文件显示:建康有密旨拟于年内废止所有地方自治实验,代之以“圣训直辖区”,由皇帝亲选儒臣治理。敦煌位列首批撤销名单。
更可怕的是,签发者竟是当今太子??那位未曾露面却始终关注西北动静的年轻人。他曾私下召见李承徽,询问“妇人立法”的细节,当时只淡淡一句:“有趣。可惜不合祖制。”
阿禾读完密件,久久不语。窗外月色如霜,照在庭院中的陶碑上,映出斑驳光影。她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雪夜,自己蜷缩在牢房角落,听着狱卒嘲笑:“女人也配谈法?等太阳从西边出来吧。”
现在,太阳确实没有从西边升起。但它照亮了一块曾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沙原,让无数双曾低垂的眼睛学会了平视世界。
次日,她召集核心团队于莫高窟密议。启明主张立即向全国发布通牒,揭露阴谋;乌仁娜建议联络北方游牧联盟,形成政治牵制;赵元礼则提醒:“一旦撕破脸,对方必以谋反罪名剿杀,百姓将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