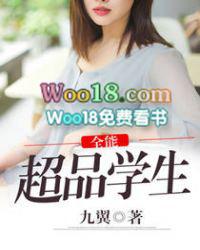宝书网>魏晋不服周 > 第214章 大郎该喝药了(第1页)
第214章 大郎该喝药了(第1页)
洛阳宫很大,天子的寝宫也很大,但卧房却很小。
司马昭被宦官搬到那间狭小的寝宫卧房之后,便鱼贯而出。
包括贾充、石守信甚至是匆匆赶来的司马炎与司马攸,都在卧房门口等待。
非传唤不得入内。。。
驼铃声断,暮色四合。敦煌城西的沙丘上,一队商旅正缓缓穿行于残阳与风影之间。领头的粟特老商人摩挲着腰间铜牌,那是共审庭授予“信义商使”的凭证,刻有“持节不欺,市无虚约”八字。他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绵延的驼队??不再是昔日只为金银奔波的货队,而是载着律书抄本、医方简册、陶板诉状的流动驿站。每至一村一堡,便有人下车宣讲《双碑定法》,教牧民如何用陶片写下冤情,如何推举三人评议团先行调解。
阿禾已不再频繁登坛主审。她将日常事务交予新晋民选律佐,自己则带着启明、乌仁娜等人巡行河西诸郡,从酒泉到张掖,从删丹到居延。她们所到之处,百姓争相聚拢,不是为了告状,而是为见证:原来法律可以不藏于宫阙,而立于井台;原来裁决不必仰赖官印,也能凭公心达成。
这一日,她们抵达焉支山南麓的羌寨。寨中长老以青稞酒相迎,席间却有人低声提及:“前月有‘赤焰营’残部流窜至此,冒充朝廷使者,强征马匹三百匹,口称‘备战高昌’。我们不敢抗命,只得献出部落过冬之畜。”
阿禾闻言未语,只让启明取出玉门关缴获的伪令符拓片,请长老辨认。果见其上印文与那日所执者如出一辙,连“河”字断裂处都分毫不差。
“他们还在活动。”乌仁娜怒极反笑,“崔琰虽罢相,爪牙未尽!”
当晚,阿禾召集寨中青年,在火塘边召开小型共议会。她问:“若再遇假令,你们当如何?”
一名少年挺身道:“按《双碑定法》第三条,凡军政干预共审、阻挠调查者,民有权联名弹劾,直达天听。我们可派代表赴敦煌递状!”
另一女子摇头:“等你走到敦煌,马已被牵走半年!依我看,应立刻成立‘边寨互护盟’,各村互通烽燧信号,一旦发现可疑军队入境,即刻鸣鼓聚众,封锁要道,同时派人飞报调查团。”
阿禾点头:“前者是理,后者是势。二者皆需。”
她提笔在羊皮卷上草拟《边民自卫约》,规定:凡遇无文书、无勘合、无地方官监临之军事调动,边境村落可行使“临时拒权”,暂扣人员物资,启动五日紧急评议程序,并向共审庭派出快骑通报。此约为防滥权,亦设反制条款??若误判属实,发起村寨须赔偿损失,并由全体陪审员公开致歉。
三日后,约成。百余名羌、汉、匈奴混居的村民在寨门前立下血誓,将一份副本封入陶罐,埋于古松之下。传说此树已有三百岁,根系贯穿山岩,能听地脉之声。
就在此时,一名浑身沙尘的信使跌跌撞撞闯入寨中,手中紧握一支断裂的节杖??正是此前前往洛阳方向探查建康密信源头的斥候之一。他带来的消息令人震骇:他们在河内郡一处废弃驿站发现了秘密档案窖藏,其中不仅有崔琰与北魏幽州刺史私通的蜡丸信,更有一份手书名录,赫然写着“河西可用之奸”四字,下列数十人名,竟多为现任州府属官、军屯校尉乃至寺庙住持!
最令人惊心的是,名单末尾另有朱批:“敦煌妇阿禾,妖言惑众,宜诱以爵禄,不成则除之。陆修文已默许。”
“陆修文?”启明几乎失声,“他曾公开退隐,怎还参与此事?”
阿禾盯着那行字,良久不动。火光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他不是反对共审,他是怕它太成功。”她缓缓道,“一个女子牵头立法,百姓自断官司,若真成了常态,儒家那一套‘礼不下庶人’的秩序就崩了。对他而言,这不是进步,是颠覆。”
乌仁娜冷笑:“所以他宁愿看着朝廷用刀剑压服,也不愿承认民间能自治一日。”
众人沉默。窗外风啸如诉,吹得经幡猎猎作响。
次日清晨,阿禾遣快骑将档案副本送往敦煌,并下令启动“清源行动”:由跨族调查团联合各地乡老,逐一对名录中人物进行背景核查,凡查实受贿、通敌或滥用职权者,一律公示姓名、事由及证据,交由共审庭裁定处置方式。行动准则只有一条:**不株连家属,不轻信口供,不以出身定罪,唯事实与程序为准。**
三个月内,十七名官员被罢免,五座军屯更换主管,两座寺庙因长期包庇贪吏被取消免税资格。但也有九人经评议后证明清白,反获补偿名誉损失金,并受邀加入监察使顾问团。民心渐稳,谣言自息。
然而真正的风暴,来自建康。
秋雨连绵之际,一艘楼船逆长江而上,直抵荆州码头。船上走出一位身着紫袍的中年男子,手持御赐金节,自称“试点监察大使”李承徽,奉旨巡视敦煌共审制度成效。随行者除十余名文书吏员外,更有禁军精锐二百人护送,阵仗远超寻常钦差。
消息传至敦煌,赵元礼连夜赶来祠堂,面色凝重:“此人履历蹊跷。早年任廷尉评时,曾力主‘庶民不得议刑’,著文痛斥‘匹夫操法柄,国将不国’。后因党争失利外放岭南,十年未获升迁。此次骤然起复,且直插我核心事务,恐非善意。”
启明翻阅其过往奏疏,冷笑道:“他还写过一句:‘妇人干政,三代之乱阶也。’想必对阿禾恨之入骨。”
阿禾却平静如常:“既然是‘奉旨巡视’,我们便以礼相待,以法相迎。”
七日后,李承徽率队进入敦煌城。迎接他的不是鼓乐仪仗,而是一座临时搭建的“民意听证坛”。坛前竖立大幅布幔,上书本次巡视三大议题:一、共审庭是否侵犯朝廷司法权?二、民选律佐是否构成非法结社?三、双碑定法是否违背现行律令?
每项议题下,悬挂数百枚陶板,皆为百姓亲笔所书意见。支持者言:“吾儿被豪强夺田,县官不理,共审三日即还。”反对者亦有:“盲童主诵春秋,岂非亵圣?”阿禾命人将正反言论并列展示,不加删改。
李承徽观之皱眉,讽曰:“此乃煽动舆情,非治国之道。”
阿禾当面回应:“大人若觉此法不合礼制,请依《共审录》规则提出质询。我们可组织专题评议会,邀儒生、法家、僧侣、商贾共议十日,最终由五百人陪审团投票裁决。您可亲自陈述观点。”
李承徽哑然。他本欲以威压震慑,却不料陷入对方的规则陷阱??若拒绝评议,则显心虚;若参与评议,则等于承认共审制度合法。
僵持三日后,他转而要求查阅全部案卷记录,声称要“评估司法质量”。阿禾欣然允诺,命人开放档案库。谁知李承徽竟带人彻夜抄录,甚至私自拓印双碑全文,意图带回建康作为“僭越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