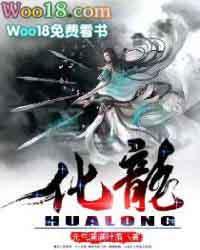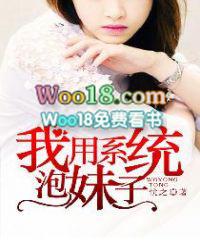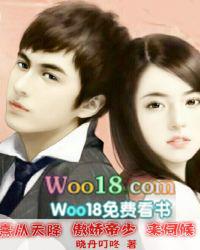宝书网>二郎至圣先师 > 330 徐公堤造福一方(第1页)
330 徐公堤造福一方(第1页)
越青云目送好友远去,沉默不语,良久后方才一声轻叹。
在他身旁,楚净璃轻声道:“石大哥吉人天相,兄长且宽心。”
越青云轻轻颔首,兄妹二人一同回到庄园。
他们没有去佛堂,在主屋落座,越青。。。
风雪渐歇,晨光破云而出,洒落在长安城外的至圣书院之上。青瓦白墙间,书声琅琅如溪流不息,穿过竹林,绕过石桥,回荡在初春微寒的空气中。李承安立于讲坛之前,身披素袍,须发已染霜雪,然目光清明如镜,映照天地正气。
今日是书院开讲《孟子》之日,三千弟子列坐堂下,或执笔记录,或凝神倾听。台阶之下,更有无数百姓携老扶幼而来,只为听一句善言,得一念清明。李承安抚须轻叹:“十年了……师父离开已有十年。”
他抬头望向院中那块“道在人间”碑文,阳光正斜斜地照在“道”字上,仿佛有金光自石缝中渗出。他缓缓开口:“诸位可知,何为‘道’?不是飞升成仙,不是呼风唤雨,而是你我心中那一念不忍??见人受苦,愿伸手相援;遇不平事,敢挺身而出。”
话音未落,忽有一阵清风穿堂而过,卷起满地落叶,竟在空中凝成一道模糊身影,似人非人,若隐若现。众人大惊欲起,却被李承安抬手制止。
“不必惊慌。”他望着那影,眼中泛起涟漪,“这是心念所聚,意之所归。当千万人共持一道,其念不灭,便可通灵达神。”
那光影微微颤动,仿佛回应。片刻后,竟化作一句低语,在所有人耳边响起:
“承安,你未曾负我。”
声音虽淡,却如雷霆贯耳。不少弟子当场泪下,伏地叩首。李承安亦跪拜于地,声音哽咽:“师父,弟子日夜讲经,不敢懈怠。天下已有书院七十二座,村塾千余所,皆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训。民间疾苦渐减,礼义复兴,人心回暖……您走时说的那句话,真的应验了。”
他顿了顿,仰头看向虚空:“只要还有人在念一句好话,做一件好事,善就在。”
光影久久不散,最终化作一片金粉,洒落碑前,渗入泥土。从此以后,每逢月圆之夜,那碑底便生出一朵白梅,清香远溢,无人灌溉,年年不绝。
与此同时,四海之内,异象频生。
北方边陲,一名少年手持竹简站在断崖之上,面对百名叛军将领。他身后是被劫掠的村庄,火光尚未熄灭,妇孺蜷缩哭泣。一名将军狞笑策马上前:“黄口小儿,也敢阻我大军去路?”
少年不退反进,朗声道:“昔有二郎至圣先师,守封印五百年,只为护一方清净;今有我辈读书之人,纵无神通,亦当以道御暴!”说罢,展开手中《太上感应篇》,高声诵读:“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刹那间,狂风骤起,天色昏沉。那些原本凶神恶煞的士兵竟纷纷丢下兵器,跪地痛哭。有人撕碎战袍,有人折断刀剑,更有数十人当场自首,愿赴官府赎罪。原来他们多为饥民被迫从贼,内心早存悔意,只缺一人唤醒良知。
南方海岛,那位佩剑少女医者已年过三十,仍孤身行医于渔村之间。她不再年轻,脸上刻着风霜,但眼神依旧清澈。这一日,她救治了一名重伤海盗,对方苏醒后欲夺药杀人逃走。她却只是静静取出那柄刻着“二郎赐”的短剑,横放于案上。
“你可以拿走它。”她说,“但请记住,这把剑从未杀过一个无辜之人。它的主人教我的第一课是:救人比复仇更重要。”
海盗怔住,良久跪倒,嚎啕大哭。后来他解散团伙,带领残部开荒种田,建起一座“赎心寨”,专收浪子回头者。寨门口立碑,上书:“此地不纳恶人,唯容悔者。”
西域深处,那位曾以《论语》退匪的老仆已然离世。临终前,他将那本破旧典籍交予孙子,叮嘱道:“书中自有光明。若世道黑暗,你就做那盏灯。”少年谨记祖训,长大后不做官,不求财,只在沙漠驿站设席授徒。来往商旅无论贵贱,皆可听他讲一段仁义之道。久而久之,这条古道竟再无大规模劫掠之事发生,人称“善途”。
东海渔村的老渔夫也已寿终正寝。葬礼当日,全村点灯三夜,海上浮光连成一片,宛如银河倾泻。他的儿子继承父志,不仅继续引航救人,更召集渔民成立“灯塔会”,每年冬汛必巡海救援。他们会唱一首古老的歌谣:
>“黑风起兮夜茫茫,
>一灯燃兮照四方。
>不求仙兮不拜皇,
>只愿人间有暖光。”
这首歌渐渐传遍沿海,成为渔民心中的圣曲。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迎来了曙光。
西北某城,豪强勾结贪官,强占良田,逼死农妇,百姓敢怒不敢言。一日,一位布衣先生悄然入城,在市集摆下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本《道德真经》与一碗清水。他不吆喝,不募捐,只是静坐诵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起初无人理会。直到第三日,一名饿晕的孩子爬到桌边,他轻轻喂水喂饼,又低声教导:“做人要有良心。”孩子含泪点头。
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穷苦人前来聆听。有人送来粗茶,有人献上野菜。第五日,竟有百余人围聚听讲。豪强闻讯震怒,派家丁砸毁书桌,鞭打众人。
当晚,豪强暴毙家中,墙上血书四字:“天理昭昭。”
官府查无可查,只得压案了事。可自此之后,每有欺压之事发生,不出三日,必有人匿名揭发,或留警语于门墙,或投书于衙前。百姓私下议论:“定是至圣先师显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