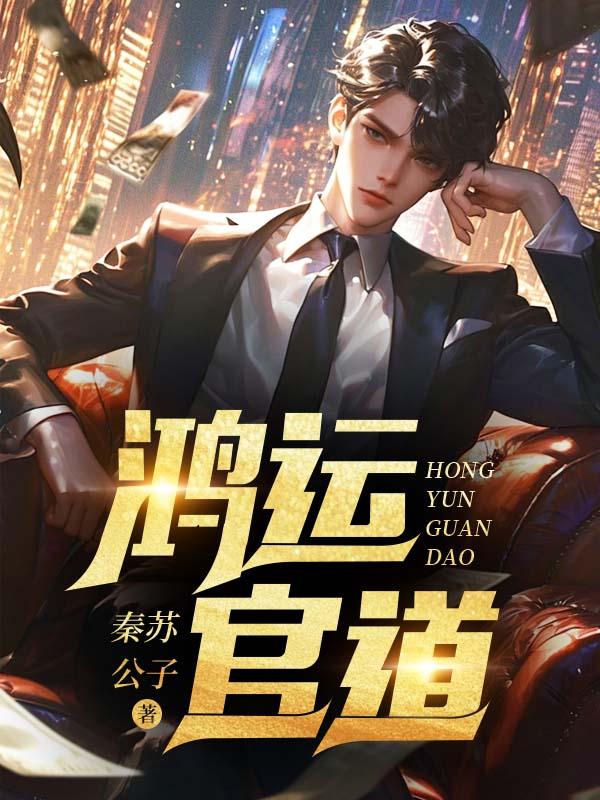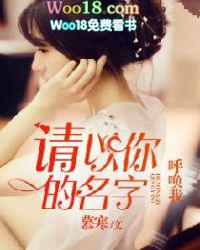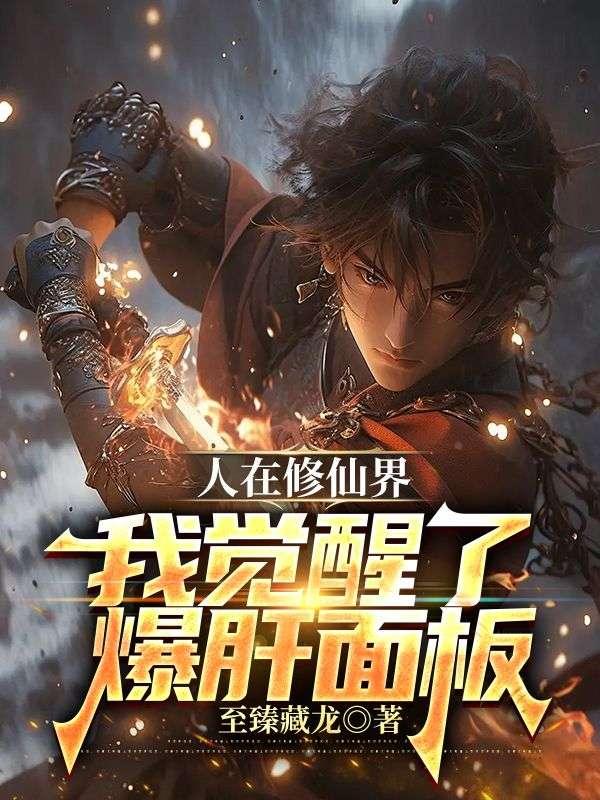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天赋异禀的少女之无相神宗 > 第533斜月山庄二百四十八(第1页)
第533斜月山庄二百四十八(第1页)
几个终极扶桑武士用手想要夺取木头人手中的兵刃,可是无论怎么用力拔,都拔不出来!
它们的手做得和人的手简直一模一样,甚至连它们的手的背部都有纹路。
山风拂过断崖,卷起一缕沙尘,在空中划出细长的弧线,如同无形之笔勾勒命运轨迹。那支被遗留在岩石上的玉笛哨,在晨光中泛着温润微光,仿佛仍存一丝余温,不肯彻底归于沉寂。日复一日,有人来寻,有人跪拜,有人试图拾起它,却总在指尖触碰的刹那心生敬畏而缩手。它不属于任何人,却又属于每一个驻足凝望的人。
岛上的日子悄然流转,如潮水般不惊不扰。学堂里的孩子已能熟练演奏《我不》的变奏曲,旋律不再只是抗议,更成了清晨上学路上的歌谣、母亲哄睡时的低吟、渔夫出海前的祈愿。声纹布如藤蔓攀爬,从村头延伸至邻岛,织成一张看不见却听得见的网,将无数微小的声音编织成时代的回响。
阿禾成了岛上最忙碌的人。她不再是那个怯生生抱着竹笛的小女孩,而是背着行囊穿梭于各村之间,教人识字、记谱、写信。她的嗓音清亮,话语朴实:“不是只有读书人才能说话,也不是只有官老爷才能定是非。你心里怎么想,就该怎么写。”她随身带着一本破旧册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地传来的消息??某地女子因拒嫁恶霸当众诵读自撰《誓不屈书》,竟引发百人联署;某镇孩童自发组织“说真话日”,老师非但未罚,反而加入其中;甚至有老妪在临终前留下遗言:“我这一生骗了太多人,最后一句,我要说真话。”
这些故事,她都会讲给纳兰歆听。
可纳兰歆总是静静听着,不多言语。她每日清晨依旧沿着海岸行走,捡拾被浪打上岸的碎木、贝壳、残布,带回村里做成乐器或装饰。她教老人用骨片制哨,教孩子用芦苇编笛,告诉他们:“声音不在长短,而在是否出自真心。”她不再吹笛,也不再引领,但她所经之处,总有新的旋律悄然萌芽。
春去秋来,第五个启声节临近。
这一年,长安传来新讯:太子亲自主持修订《礼经》,以《众生谱》残卷为基,融合民间陈情、地方歌谣、百姓家训,历时三年终成《新礼》十二篇。书中首章开宗明义:
>“民之声,国之脉也。堵则瘀,疏则通。故治世者,不当惧言,而当修耳。”
皇帝阅后沉默良久,最终提朱笔批曰:“准行。”并下诏废除“静口税”,赦免最后一批缄音司旧案囚徒,命史官重修言论史,列为国鉴。
与此同时,“言路院”已在七州推行,百姓可凭“言帖”入京陈情,凡涉民生疾苦、政令弊端者,皆得面奏三日之内回复。更有奇者,每逢朔望,宫门前设“无声坛”??一块黑色石台,任何人皆可登台书写心声,不论褒贬,不得抹除。短短数月,石台已被层层叠叠的文字覆盖,墨迹斑驳,宛如一部活的历史。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迎来了春风。
西北边陲,一座名为“哑城”的古邑仍禁声如铁。此地原为流放之地,百年来由一位世袭镇守将军掌权,其家族世代效忠皇室,对“启声”之举深恶痛绝。他下令焚毁所有传单,拆毁民间乐器,甚至以“惑乱民心”罪名处决了几名传播《我不》歌谣的少年。城中百姓噤若寒蝉,连咳嗽都要掩口。
消息传到孤岛那夜,海面骤起狂风。
纳兰歆立于崖边,衣袂翻飞,目光穿透风雨,望向远方。她没有动怒,也没有召集众人议事。次日清晨,她只是取出一支新削的竹笛,交给阿禾:“送去哑城的孩子们手里。”
阿禾不解:“只是一支笛?”
“是种子。”她说,“风会带它进去,孩子会把它藏进袖口、枕头、鞋底。只要有一个孩子愿意吹响,整座城就会醒来。”
于是阿禾启程。
她扮作游方医女,背篓里藏着十支同样的竹笛,一路西行。途经荒漠、驿站、关卡,每到一处,便悄悄留下一支笛子和一张纸条:“你可以不说,但你不该被堵嘴。”有些村庄无人回应,有些则在她离开后传出断续笛音,像是试探,又像呼唤。
抵达哑城时,已是寒冬。
城墙高耸,门禁森严,巡逻士兵手持铁棍,专查携带乐器者。阿禾无法进城,只得在城外村落暂居。她开始教村童识字,唱些看似无害的童谣,实则暗藏节奏与隐喻。她在雪地上画音符,用树枝敲击冰面演示节拍,孩子们好奇模仿,笑声惊飞了屋檐上的乌鸦。
某夜,一名瘦弱男孩偷偷来找她,手中紧握半截断裂的竹管。“姐姐……这是我爹留下的。他在牢里……临死前咬破手指,在墙上写了‘我想听女儿唱歌’……后来,她们再也不敢开口了。”
阿禾心头剧震,轻轻接过那截竹管,连夜修补,调音,交还给他:“现在,你可以替他听见。”
三天后,第一声笛响从城郊孤儿院传出。
起初微弱,颤抖,似怕惊扰黑夜。但很快,第二声、第三声接续而起,合成了《我不》最初的旋律。守军闻声赶来,砸碎窗棂,夺走乐器,鞭打孩童。可第二天,更多孩子躲在柴房、井底、灶台后继续练习。他们不再用笛子,改用口哨、拍掌、踩地发出节奏。整个冬季,这座死寂之城的地底,仿佛有无数细小的鼓点在跳动。
开春之际,一场大雪封山。
粮道中断,城中饥荒初现。镇守将军欲强征周边村落存粮,激起民怨。就在冲突爆发前夕,一群孩子突然出现在城门口,每人手中捧着一只陶埙,齐声吹奏《新礼》第一章的配乐??那是他们在声纹布上反复聆听学会的旋律。
士兵举矛欲冲,却被身后异动惊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