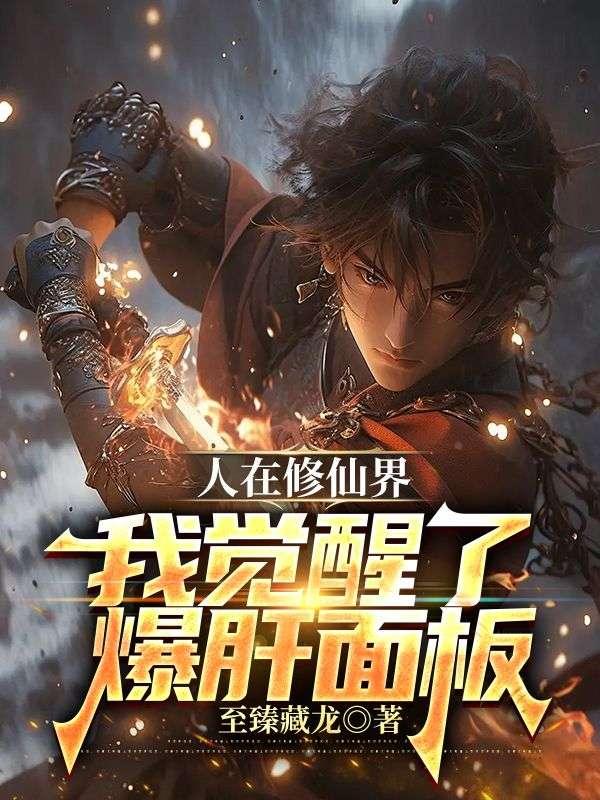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离柯南远一点 > 652 遗憾终须在现实中弥补(第1页)
652 遗憾终须在现实中弥补(第1页)
姓名冈仓政明,明面上的身份是为某位政要当秘书,但实际的身份是组织安排的间谍……
此刻,在这七夕节的当日,当高远以酒店服务员的身份敲开了此人租住的房间大门之后,借机进到了房间内的高远,确认了该房间。。。
夜深了,东京的灯火如星子洒落人间。毛利兰站在自家阳台,望着远处热带乐园的彩灯在黑暗中闪烁,像是一颗不肯熄灭的心脏。她披着薄毯,指尖轻轻摩挲胸口??那封信还在那里,纸页已微微泛黄,却依旧温热,仿佛藏着一个不肯离去的灵魂。
风起了。
她忽然听见一声极轻的钟响,不是从耳中传来,而是自心底升起,像是某种遥远的共鸣穿透了时间与空间的缝隙。她的呼吸一滞,睫毛微颤,眼前的世界似乎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
“新一……”她喃喃。
没有回应,也不需要回应。她知道他在哪里。在每一个孩子笑着说出“谢谢元太哥哥”的瞬间,在每一对母子相拥而泣的梦境里,在那些本该遗忘却被温柔唤醒的记忆深处??他从未离开。
而此刻,京都地底,青铜门静默如初,水晶柱却悄然亮起一丝微芒。久川绫的身影浮现在虚空之中,白袍飘动,面容冷峻却又难掩悲悯。她低头看着脚下石台上那具瘦弱的身体??工藤新一蜷缩着,呼吸微弱得几乎察觉不到,手中仍紧紧攥着一枚玻璃瓶,瓶中那粒发光的沙正缓缓跳动,如同最后的心跳。
“你已经透支到了极限。”久川绫低声说,“共感网络不再需要你亲自维系。千夏和觉醒者们正在接力,记忆的河流已经开始自我流动。”
新一没有睁眼,只是嘴角轻轻扬起:“可我还想再送一个人回家。”
“谁?”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住在格陵兰岛边缘的因纽特村落。她梦见自己死于雪崩的母亲,但醒来后却哭着说‘妈妈不记得我了’。她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让妈妈忘了她……”他的声音断续如风,“我要让她知道,不是她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太容易忘记爱。”
久川绫沉默良久,终是叹息:“你总是这样,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宿命。”
“因为我记得那种感觉。”他睁开眼,目光清澈如少年时,“当年我在纽约,亲眼看着那个女人被推下楼,却救不了她。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活着的人再也叫不出死者的名字。我不想再让任何人经历那样的孤独。”
他说完,眉心骤然亮起一道银蓝色的光纹,如同钥匙开启无形之门。一股庞大的意识流自他体内涌出,顺着地下脉络奔腾而去,跨越海洋、冰原、沙漠,最终抵达北极圈内一座小小的木屋。
屋内,小女孩正蜷缩在床角发抖。她名叫努卡,母亲三年前为救她而死于雪崩。村里人都说她是“被雪神惩罚的孩子”,连父亲也渐渐疏远她。她每晚都会梦到母亲模糊的脸,想要呼唤,却发不出声音。
直到今夜。
风突然停了。
窗外,极光缓缓凝聚成一座钟楼的轮廓。门开处,一个戴眼镜的男孩走了出来,蹲在她面前,轻轻握住她冻红的小手。
“你妈妈记得你。”他说,“她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对风说的:‘替我抱紧努卡。’”
女孩睁大眼睛,泪水滚落:“真的吗?”
“真的。”男孩微笑,“而且她希望你知道,她爱你,比整个北极的星光加起来还要多。”
话音落下,一道温暖的光笼罩了她。她看见母亲站在雪地里,朝她挥手,嘴唇开合,无声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没能陪你长大。”
然后,她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努卡第一次主动走出屋子,扑进父亲怀里,用因纽特语哽咽道:“爸爸,妈妈回来了,在梦里。”
父亲怔住,随即泪流满面。
而在全球共感网络的数据终端上,宫野志保盯着屏幕,手指微微颤抖。
>**【记忆修复事件新增:1】**
>**【情感共振强度:9。8级(历史最高)】**
>**【目标个体脑波同步率:100%】**
>**【施术者生命体征:濒临崩溃】**
“他疯了吗?”她猛地站起身,冲向通讯器,“千夏!新一快不行了!他刚刚强行打通了一个高纬度孤立节点,耗尽了所有储备能量!”
千夏正在北海道的观察站调试设备,闻言脸色骤变。她立刻启动紧急传输协议,却发现新一所在的遗迹已被共感场反向封锁??是他自己设下的屏障。
“他不想让我们救他。”千夏闭上眼,声音沙哑,“他说过,最后一次梦,必须完整。”
与此同时,贝尔摩德驱车疾驰在京都山路上。她咬着烟,眼神凌厉,车载电台不断播报异常现象:
“……西伯利亚儿童集体绘制相同壁画,内容为‘眼镜男孩带领孩子们穿越火焰之门’;澳大利亚原住民长老称祖灵预言应验,‘记忆使者归来’;南极科考站检测到地磁波动,频率与钟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