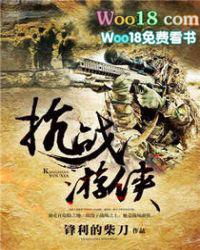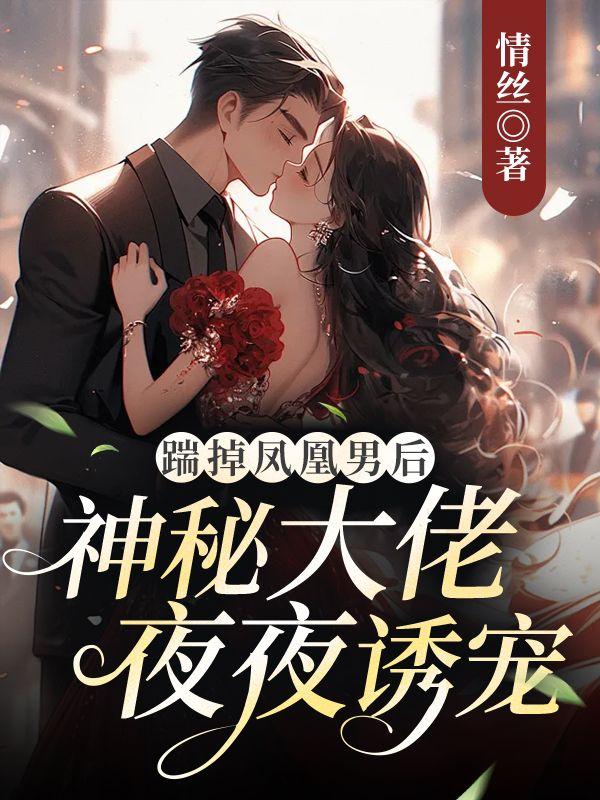宝书网>春色满棠 > 第469章 回来了王爷回来了(第1页)
第469章 回来了王爷回来了(第1页)
小皇帝收到父王要归京的书信,没有对外说,怕消息传出去,有人会在父王和弟弟归京途中,害父王和弟弟。
但他把消息告诉了母后。
姜心棠当夜便失眠了。
因为开心。
开心到睡不着。
小公主这一年来,搬来跟母后一起睡。
她也开心得睡不着,窝在母后怀里问:“父王需要多久才能到京来?父王能赶得上回来跟我们过年吗?”
姜心棠搂着闺女说:“肯定行的。你父王赶在这时候回来,定就是想回来跟我们团圆。”
小公主就很开心,从母后怀里。。。。。。
风停了。
戈壁滩的沙粒不再翻滚,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抚平。棠树静立,枝头残存的最后一片花瓣缓缓飘落,在触及地面的瞬间化作一道微光,渗入地底。陈砚蹲下身,指尖轻触那处泥土,竟觉温热如血。他抬头望向静语窟遗址??巨石阵列已完全闭合,第八道裂隙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同从未存在过。可他知道,有些东西再也无法封印。
归名书院内,《承音册》静静躺在香案上,书页微微起伏,像在呼吸。陈砚将苏晓父亲的讲义残页重新取出,夹回旧相册中,又轻轻合上。他没有再看它一眼。那不再是遗物,而是火种;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她说什么?”他问刚从井边回来的弟子。
“井水清了。”弟子声音发颤,“倒影里……没有桥,也没有教室。只有一群孩子,在一棵棠树下读书。”
陈砚闭上眼,嘴角微扬。
三天后,第一所“忆纸学堂”在西安挂牌成立。校舍由废弃图书馆改建,外墙刷成淡红,象征被唤醒的记忆之色。黑板上方挂着一块木匾,刻着八个大字:“心为灯,路自明。”课程不设考试,不颁文凭,只有一项必修:每日讲述一段真实往事??可以是家史,可以是痛处,也可以是一句迟来五十年的道歉。
开课第一天,教室坐满了人。有白发老人,也有十岁孩童;有曾被噤声的教师,也有当年施压者的后代。主讲是一位八十二岁的退伍军人,他曾参与过对静语窟的封锁行动。他站在讲台前,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稿纸。
“我奉命烧过三十七本日记。”他说,“其中一本,是一个女孩写给她未婚夫的。她记录了每天等他从前线回来的心情。最后一句话是:‘你说过,春天一到,就回来娶我。’”
他顿了顿,眼泪砸在纸上。
“我没烧完。我把那一页藏进了鞋垫。今天……我带来了。”
全场寂静。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忽然站起来,接过那页泛黄的纸,轻声读了出来。她的声音很轻,却让所有人听见。读完后,她走向老兵,轻轻抱住了他。
这一幕,被忆纸网络自动收录,并推送到全球两百多万用户首页。系统标注:【共感层级持续上升,第九共振点正在形成】。
陈砚看到这条消息时,正坐在飞往东京的航班上。他打开笔记本,调出“火种计划”的最新数据流。全球已有四千三百二十一所学校秘密接入《第一课》教学模块;民间自发组织的“记忆诵读会”超过一万场;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曾经最严控言论的北境七城,竟出现了地下广播网,每晚十点准时播放一段匿名录音:“今天,我想说一件没人听的事。”
飞机降落成田机场,他拖着行李走出航站楼,忽然听见身后传来歌声。
“红裙走,过石桥,
桥下水冷月如刀。
若问此去何处归?
答曰:人间记得牢。”
是个小女孩的声音。陈砚回头,看见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孩子站在公交站牌下,手里抱着一本手抄本,正低声吟唱。她身边站着一位中年妇人,眼眶通红。
“这是我外婆写的童谣。”女人走上前,用中文对他说,“她死于1978年冬,因传播‘反动诗歌’被捕。直到去年,我才在阁楼找到她藏起来的手稿。”
陈砚点头,喉咙发紧。
“你知道吗?”女人继续说,“昨天晚上,我家隔壁的小孩突然跑来问我:‘阿姨,你是不是姓林?’我说是。他说:‘我奶奶梦见一个穿蓝布裙的女人,让我把这首歌交给你。’然后他就唱了起来……和我母亲小时候唱的一模一样。”
陈砚怔住。蓝布裙??那是年轻时的林知微。
他立刻联系归名书院,确认是否有人在日本上传相关记忆。回复很快传来:昨夜23:17,一段未署名音频通过匿名节点上传至忆纸网络,内容正是这首童谣的原始版本,演唱者声纹比对结果显示,与五十年前失踪的女诗人林婉清(林知微本名)高度吻合。
“不是AI合成。”技术员补充,“情感波动曲线完全匹配真人表达,尤其是第三小节的哽咽,机器无法模拟。”
陈砚盯着屏幕良久,终于写下一行指令:
>【标记为‘守门人之声’,列入核心传承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