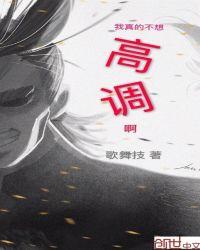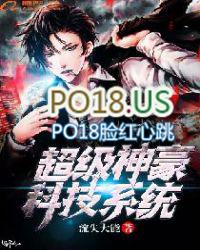宝书网>刑警日志 > 第1935章 叉车司机庞云(第2页)
第1935章 叉车司机庞云(第2页)
他忽然抬起头,眼中布满血丝:“我气不过,推了他一下……他撞到货架上,倒下去就没再起来……我吓坏了,赶紧把他拖进库房藏起来……我以为他只是晕了……真的……”
“那你为什么撒谎逃跑?为什么不报警?”杨森质问。
“报警?”周志国苦笑,“谁信一个瘸子的话?再说我翻墙进来本来就不合法,要是被抓,别说工作,还得坐牢……我只想悄悄处理掉……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法医最终出具报告:死者张建国系后脑撞击货架致颅骨骨折、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外力作用符合钝器撞击特征,与现场货架腿脱落油漆位置吻合。烟蒂DNA与周志国完全匹配,鞋印、布条血迹亦为其所留。
证据链闭环。
案件告破当晚,杨森独自坐在办公室,窗外雨势渐大。桌上摊开着周志国的笔录复印件,旁边是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三年前物流园年终聚餐的合影。照片里,周志国站在人群边缘,笑容拘谨;而张建国搂着主管肩膀,啤酒举得高高的,满脸得意。
命运的齿轮往往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悄然转动。一句轻蔑的嘲讽,一次无助的推搡,一场沉默的掩盖,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三天后,支队召开结案通报会。陆川总结道:“本案警示我们,基层劳动者的职业保障与心理健康不容忽视。一个被系统抛弃的人,可能会用极端方式寻求回应。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破案,更是预防。”
会后,杨森和杨林驱车重返南郊物流园。夕阳西下,园区恢复了往日喧嚣。叉车轰鸣,货车穿梭,工人们喊着号子装卸货物。仿佛那起命案从未发生。
但他们知道,每一处阴影背后,都藏着未被倾听的声音。
“你说,如果我们早点关注这些边缘人,案子会不会不一样?”杨林望着远处围墙,喃喃道。
杨森没回答。他只是默默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任风吹散烟雾,如同吹散那些沉重的记忆。
几天后,市局发布新规:全市重点用工单位须建立离职员工回访机制,定期排查高风险人群心理状态;同时推动“零工驿站”建设,为失业人员提供临时岗位对接服务。
而在废弃化肥厂东侧那间空荡的小屋里,一只搪瓷缸静静摆在窗台。缸底积着雨水,映着天空微光,像一颗未曾熄灭的眼睛。
某日凌晨,环卫工人在路边垃圾桶发现一本烧焦一半的日记本。残页上写着:
“今天去找了老刘,他说主管不肯让我回去。我说我还走得动,他说我看不清货单。我想哭,可眼泪早干了。他们把我当垃圾扔掉,可我明明还想活着啊……”
这行字下面,反复涂改着一句话: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真的不想……”
该日记本经鉴定确系周志国笔迹。目前已被列为案件附属材料封存。
数月后,一起类似未遂案件在邻市告破。嫌疑人是一名被辞退的夜班保安,因情绪失控持刀闯入former雇主办公室,幸被及时制止。警方调查发现,此人曾在社交媒体浏览过“刑警日志”相关报道,并留言:“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这条留言引起公安部关注,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蓝盾倾听计划”,旨在通过大数据预警+社区干预,提前识别潜在暴力风险个体。
杨森的名字,出现在该项目首批专家顾问名单中。
某个周末,他带着儿子参观警察博物馆。在一角展柜里,陈列着那双42码的黑色劳保鞋,标签写着:“2023?南郊物流园杀人案关键物证”。
孩子仰头问他:“爸爸,穿这双鞋的人,是不是很坏?”
杨森蹲下身,轻轻抱住儿子:“有些人不是天生坏,而是太久了没人愿意听他们说话。所以,你要学会倾听,哪怕对方说得很难听。”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阳光透过玻璃洒在鞋面上,那菱形格纹路依旧清晰,仿佛仍在诉说着一段无人知晓的跋涉。
夜深人静时,杨森伏案写下新的办案笔记:
“每一个罪犯的背后,都有一个未被讲述的故事。我们的职责,不只是追捕黑暗,更要照亮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笔尖顿了顿,他又添了一句:
“正义不止于判决,更在于不让下一个‘周志国’走上绝路。”
合上笔记本,他望向窗外。城市灯火通明,万家安宁。
他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