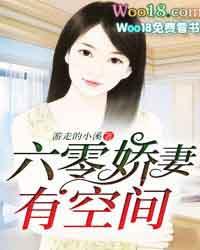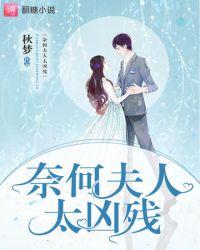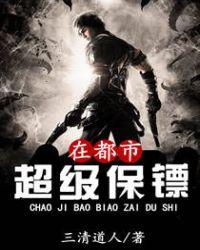宝书网>大唐:太平公主饲养指南 > 第五百章 清和姬(第1页)
第五百章 清和姬(第1页)
杨易手中的青龙镇水师所掌握的兵器,当然要比骆玉蛟手中的还要强大。
骆玉蛟虽然深受杨易的信任,但是手底下那帮人毕竟不是杨易自己亲自带出来的兵马,所以当然不可能把最新式精锐的武器交给他们。
当。。。
春深三月,启唇谷的答心花开得漫山遍野。晨雾未散,花瓣上露珠轻颤,映着初升的日光,宛如无数微小的铃铛在风中低语。村口老槐树下,几个孩童围坐一圈,正学着大人的模样,轮流说“我昨天害怕的事”。一个瘦弱男孩支吾良久,终于开口:“我……梦见爹被狼叼走了。”话音落,身旁女孩轻轻握住他的手:“我也梦见过。”无人嘲笑,无人打断,只有一阵风吹过草尖,带起一片细碎银光。
这一幕被路过的驿使看在眼里。他本是奉命前往西域传递国书,途经此地原打算歇脚饮马,却驻足良久。他想起自己幼时因家贫卖身为仆,夜里尿床遭主母鞭打,从此再不敢提一句冷、一句饿。如今已为朝廷信使,穿锦袍、骑骏马,可心底那道伤疤从不曾愈合。此刻望着孩子无邪的脸,他忽然觉得喉头一紧,眼眶发热。
他解下水囊,蹲下身,对那男孩轻声问:“你现在还怕吗?”
男孩摇头:“不怕了。绿蘅婆婆说过,梦不是真的,但你说出来,它就再也不能咬你。”
驿使怔住。他记得这个名字??终南山那位守铃的老婢,传说她死后化作了听心草的根。他曾在边关驿站听过一则奇事:一名戍卒夜夜噩梦惊醒,自暴自弃,直到某日收到一封匿名信,上面只有五个字:“你怎么了?”他哭了一整晚,次日竟主动报名去最险的哨岗巡防。后来才知道,那封信是从长安一位失语多年的贵妇人手中寄出的,她写完后第一次笑了。
驿使默默将一枚铜钱放入孩童手中的陶碗??这是新制的“言币”,专用于“静语园”体系下的言语疗赎仪式,象征话语的价值不亚于粮食与刀剑。他起身欲行,忽觉袖中一震,探手取出,竟是随身携带的竹筒里,那卷誊抄的《心政实录》残章无风自动,纸页翻至阿芜亲笔那一段:
>“一切苦难,始于不说;一切解脱,始于开口。”
他猛然记起此行任务:护送一份密档赴安西都护府,内有三十六名前朝余党供词。这些人口供奇特,不谈谋逆细节,反倒详述童年遭遇??有人七岁目睹母亲被充为官妓,有人十岁被迫食犬肉以活命,有人十五岁亲手勒死亲弟以防其落入敌军之手。审讯官不解其意,呈报中枢,皇帝阅后沉默半日,批曰:“非罪状,乃心疾。送‘静语园’调理。”
驿使心头如雷击。他忽然明白,这哪里是叛乱余孽?分明是一群从未被人问过“你怎么了”的魂灵,在黑暗中挣扎了半生。
他调转马头,不再西行,而是折返长安。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做一只传话的鸟。他要亲自走进紫宸宫外那座新立的“言政院”,请求面见天子。不是作为信使,而是作为一个曾把恐惧咽进胃里三十年的人。
与此同时,长安城南,“静语园”深处一间青瓦小屋内,一名年轻男子正伏案疾书。他是当年奸细之后,如今已是“倾听使”中的骨干。昨夜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火海之中,四周女尼手牵手围成圆圈,齐声诵经,火焰竟绕行不侵。其中一人转身望他,面容竟与记忆中素未谋面的母亲相似。醒来时,泪水浸湿枕巾。
他写下一篇《忏悔录补遗》,不再仅谈自己如何背叛朝廷,而是追述幼年如何被养父灌输仇恨:“他说,所有点灯的人都该死,因为他们照亮了别人看不见你的存在。所以我恨光,也恨说话的人,因为声音让我显得多余。”他写道:“我终于明白,我不是天生恶人,我只是太早学会了闭嘴。”
文书封缄完毕,投入院中特设的“心炉”。火焰腾起瞬间,屋顶光影再现莲形,比往常更大、更久。值守的倾听使记录道:“昨夜心炉显相,持续十二息,创纪录。”
此事传至皇宫,皇帝正在御花园练习“倾听呼吸法”??这是近年由龟兹乐师传入的新术,借音乐节奏调节情绪,助人平静开口。他闻报沉吟片刻,命人取来近年来各地“沉默名录”的汇总卷宗。翻开第一页,便是慈音庵七十二位女尼的陈述全文。他逐字读完,忽然掩卷长叹:“朕登基以来,平叛乱、修水利、开科举,自以为功德累累。可若非那一声铃响,朕连她们的存在都不知。”
他召来柳明远。老学士已退居二线,但仍每月入宫讲授“言语伦理”。两人相对而坐,茶烟袅袅。
“先生以为,如今天下,真能人人开口否?”皇帝问。
柳明远抚须微笑:“陛下可见过春蚕吐丝?起初细若游丝,无人在意。可千蚕共作,终成锦绣。今日之民,尚有惧言者、羞言者、不知如何言者,然种子已播,根脉已通。十年二十年后,必有代代相传之习性??遇人困厄,先问‘你怎么了’,而非断其是非。”
皇帝点头,忽又皱眉:“可近日有奏报称,北疆某屯田营军官禁止士兵诉苦,谓‘动摇军心者斩’。更有地方官将‘静听廊’举报信焚毁,称‘尽是妇孺哭诉,不堪入目’。”
柳明远神色不变:“正如春雷之前必有蛰伏。旧习难改,非一日之功。然只要制度在,火种不灭,终将燎原。”
临别时,皇帝赠他一方新制玉佩,雕作铃形,内嵌一缕银丝??正是当年铜铃熔铸后重炼所得。背面刻八字:“声入心,心成政。”
柳明远归家途中,路过国子监。昔日门生如今多为朝中要员,见老师归来,纷纷迎出。有人禀报:今科进士策论题目为《论“言疗”与治国之道》,考生答卷精彩纷呈。一名寒门学子写道:“臣幼时家贫,父常醉酒殴母。每欲劝阻,辄被斥‘小儿何知’。直至去年参加乡里‘言语会’,听人讲述类似经历,方知非我一家之痛。今愿为官,首务非征税缉盗,而在设立‘儿童言室’,让天下孩童皆有处说怕、说疼、说委屈。”
柳明远读罢,老泪纵横。他命人将此文抄录百份,分送各州县学宫。
而就在同一时刻,东海之滨,一艘归航商船缓缓靠岸。船主乃江南巨贾,此番远航至扶桑,带回一批漆器与佛经,却最珍视一卷竹简??据说是东瀛“静语亭”中百年积累的悔语录。其中一段令他彻夜难眠:
>“吾少时妒兄承业,遂诬其盗米,致其被逐出家门。二十年后方知,当日家中确少粮,乃我母暗藏以济邻人。兄实无辜。今吾富甲一方,兄却沦为乞丐。吾每见其蜷缩桥洞,便觉舌如火烧,却始终不敢相认。”
商人出身寒微,少年时亦曾为争一口饭陷害同窗,致使那人终身残疾。此事埋藏心底四十余年,从未与妻儿提及。此刻读罢,如遭雷击。他当即命人备轿,直奔当年书院旧址。寻访良久,终于在城郊破庙找到那位同窗??白发苍苍,独腿跛行,靠替人抄经度日。
商人跪地叩首,泣不成声:“是我害了你……我一直不敢说……”
老人抬头,浑浊双目静静注视他良久,忽而一笑:“我知道是你。”
商人愕然:“你……知道?”
“那年你眼神飘忽,汗出如雨。我说不出证据,但我感觉到了。”老人轻声道,“可我也一直没说,因为我怕,一旦揭穿,你就再不会给我施舍的铜板。”
两人相视良久,终于抱头痛哭。商人当场写下契书,将其子过继为老人养孙,并捐资兴建“悔语堂”,专收那些背负隐罪却无处坦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