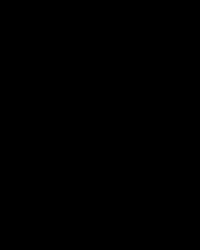宝书网>逍遥四公子 > 第1966章 此人品行不端万不可成为王夫(第3页)
第1966章 此人品行不端万不可成为王夫(第3页)
人群发出低笑。
官员脸色铁青,正要发作,忽觉袖中一轻。他低头一看,那卷竹简竟不见了。转头望去,只见一个十岁女孩正捧着竹简,一字一句读道:
>“凡民间言语,须经安语司审定,违者以惑众论罪……”
她抬头问:“叔叔,这条法令,是你写的吗?”
“自然不是!这是祖制!”
“那……你小时候说过谎吗?”
官员一愣。
女孩继续说:“我弟弟发烧说不难受,我娘做饭说不累,我爹被打说不疼。我们都学会了不说实话。可后来我发现,不说实话的人,心会烂掉。”
她把竹简递还回去:“如果你也觉得这句话该改,请你把它带回京城。如果不敢,那就留在这里吧。”
官员盯着竹简,久久不动。最终,他将其卷起,却没有收回袖中,而是轻轻放在石碑前。
“我……会上奏陛下。”他说完,转身离去,脚步踉跄如醉。
三年后,朝廷颁布新法:废除《安语法典》,设立“言权司”,专司保护公民自由表达之权。首任司官竟是当年那位黑袍使者首领。他在就职演说中只说了一句:
>“我曾以为秩序高于一切,直到我发现,没有真实的秩序,不过是精致的牢笼。”
又十年,天下大治。城郭安宁,市井繁华,百姓不仅能言,且敢言。有人批评官吏,有人讽刺诗赋,甚至有孩童编排皇帝打呼噜的童谣,传唱街头。朝中大臣欲治罪,皇帝却笑道:“让他们说吧。若朕连这点声音都听不得,岂配坐这龙椅?”
唯有极北之地,仍有零星传闻:夜深人静时,荒原上会响起若有若无的歌声,歌词无人能懂,却让听者泪流满面。猎户说,那是亡魂在呼唤名字;僧人说,那是大地在诵念真言;而归尘知道,那是语核的余波,仍在清理残存的毒素。
他终其一生守在山谷,教孩子们写字、说话、提问。他不再追问自己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明白:名字可以被夺走,但声音一旦发出,便永远属于天地之间。
临终那夜,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花海中,四周开满了看不见的花。风拂过耳际,送来无数熟悉的声音:
豆芽笑着说:“我说错了,但我没闭嘴。”
小满吹响骨笛,旋律中藏着一句:“我宁愿痛,也不要忘。”
阿枝拄拐而来,轻拍他肩:“你回来了。”
他醒来时,窗外晨光初现。他用尽最后力气,在床头木板上刻下两字:
>**我在**。
然后闭上了眼睛。
葬礼那日,没有悼词,没有哀乐。人们轮流走到他坟前,说一句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的话。有人说“谢谢你记得我”,有人说“我也曾想逃”,有个小女孩趴在他墓碑上小声说:“爷爷,我昨天说了实话,我妈打了我,但我还是不怕。”
风掠过山谷,卷起草屑与花瓣,飞向远方。
多年以后,新一代的孩子们在课本上学到这段历史。老师问:“为什么言树消失了?”
一个学生举手回答:“因为它不需要存在了。当我们都能自由说话时,就不需要一棵树来提醒我们该怎么做了。”
老师微笑点头。
放学后,孩子们奔跑在田野间,手中拿着纸笔。其中一个停下脚步,仰头望天,忽然大声喊道:
“喂!我今天吃了糖!我很开心!你能听见吗?”
没有人回应。
但他知道,有人听见了。
因为风,忽然停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