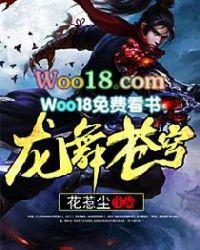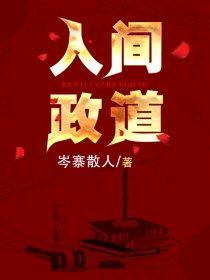宝书网>逍遥四公子 > 第1955章 西凉使者(第2页)
第1955章 西凉使者(第2页)
“不必送去。”她说,“真正的历史,不该由帝王书写。”
春去夏来,天下渐安。微光屋已成寻常,各地“校经会”日益壮大,甚至开始编纂《守望录》注疏本,称为《薪火集解》。更有好事者将其译为西域诸语,传入吐蕃、回鹘,乃至波斯商旅口中。据说大食国某位学者读罢潸然泪下,叹曰:“此非政令,乃人道之基也。”
然而太平之下,暗流未息。
秋末某夜,一名衣衫褴褛的老僧自西域而来,叩响书院山门。他双目失明,手持一根铁杖,杖头刻着一只展翅乌鸦。
沈知白警觉上前:“你是谁?”
老僧不答,只从怀中取出一枚漆黑陶铃,递出。
小满见铃,脸色骤变。
那是“哑铃”??心渊书院最古老的信物之一,二十年前随三位失踪长老一同湮灭于宫变之中。传说此铃一旦响起,必有人死于非命;若落入敌手,则预示大劫将至。
“这铃……怎会在你手中?”她声音低沉。
老僧缓缓开口,嗓音沙哑如砂石摩擦:“三位长老未死。他们被困在皇宫地底‘幽言狱’中,每日被迫抄写伪经,磨尽神志。此铃,是他们以骨髓为墨、肋骨为笔,在最后一夜刻成,托付给我带出。”
众人哗然。
“幽言狱?”沈知白怒极反笑,“朝廷竟敢私设刑牢,囚禁贤者?”
“不止如此。”老僧继续道,“狱中有井九眼,皆连地下墨脉。你们的‘墨泉计划’虽妙,却不知官府早已察觉,反向利用药墨追踪信使踪迹。已有十七名骨干被捕,关押其中。更可怕的是……他们正在复制‘心音沙’。”
“什么?”小满猛地站起。
“礼部尚书联合钦天监,召集百名工匠,试图仿制你们的陶铃。他们抓来聋哑孩童,强迫其聆听‘真话献礼’中的声音,再以酷刑提取记忆碎片,炼制成‘伪心音沙’。他们要造出能操控人心的‘御铃’。”
空气骤冷。
豆芽失声道:“那岂不是……用我们的信仰,反过来奴役百姓?”
“正是如此。”老僧点头,“他们称其为‘顺民之音’。一旦成功,天下将不再有质疑之声,人人皆成提线木偶。”
小满闭目,指尖抚过母亲留下的玉铃。她想起小荷临别所说:“真正的重逢,在心意相通。”
而现在,有人正企图斩断这份相通。
她睁开眼,目光如刀。
“我们必须救他们。”她说,“不只是三位长老,还有那些孩子,那些被囚禁的兄弟姐妹。这一战,不是为了反抗,而是为了守护‘说真话’的权利不被玷污。”
沈知白沉声问:“如何进宫?九重宫阙,机关密布,鸦影卫日夜巡防,连飞鸟难入。”
小满望向北方,那里曾有极光降临。
“我们不用进去。”她说,“我们可以让整个天下,一起震动。”
三日后,心渊书院发布“千铃令”:凡持有陶铃者,无论身处何地,皆于冬至子时齐摇铃声,持续一炷香时间。不论目的、不论信仰,只为此刻共鸣。
消息如野火燎原,迅速传遍四海。
与此同时,小满命药师连夜改良“心音沙”,加入微量银粉与冰蚕丝灰,使其遇热则发出肉眼不可见的荧光。随后,她将这批新沙秘密注入三千信使饮水中,并派阿枝带领一支轻骑,潜入京城周边,将特制药墨埋入三百余口古井底部。
“我们要让他们的‘御铃’,变成自己的催命符。”她冷冷道。
冬至夜,寒风凛冽。
子时一到,万籁俱寂。
忽然,自岭南始,一声铃响划破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