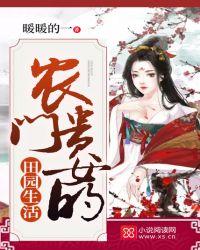宝书网>逍遥四公子 > 第1954章 神秘失踪(第2页)
第1954章 神秘失踪(第2页)
七日后,第一封回信抵达。来自江南乌镇的一位盲眼说书人写道:
>“贵处所传《薪火卷》第三章,与我十年前亲耳听小满先生讲授者不符。彼时言‘官可欺天,不可欺民’,今本作‘官宜导民,以安天下’。前者如刀,后者似棉。刀虽痛而醒人,棉虽暖而致昏。我宁信其痛,不信其暖。”
紧接着,西北敦煌一位壁画匠人寄来摹本:他在一座废弃佛窟内发现了刻于壁上的《守望录》全文,年代测定为二十年前,正是心渊书院初建之时。文中字句与现存母本完全一致,唯独无任何删节。
“原来有人早已将书刻进了石头。”阿木感叹。
“不止石头。”小满轻声道,“还有冰、有沙、有歌谣、有梦话。只要人心不死,文字就不会亡。”
与此同时,李公公悄然来到书院,趁夜求见小满。
两人在后山枯井旁相见。月光斜照,井沿青苔泛着冷光。
“我知道你发现了。”他声音沙哑,“我不否认,我让人改了几处措辞。但我是为了保全大局!如今北狄虽退,朝中鹰派已视你们为‘民间结党’,礼部尚书私底下称你们是‘白衣干政’!再这么下去,一道圣旨就能毁掉一切!”
小满静静听着,然后反问:“那你告诉我,乌镇那位说书人,敦煌那位画师,他们没见过你,没听过你的解释,为何能准确指出错在哪里?”
李公公一愣。
“因为他们心中有本真经。”小满仰头望月,“你怕火太大,可你忘了,火之所以不灭,正因为它会自己选择方向。你删一句,它从另一处冒出来;你堵一道口,它就裂开十道缝。这不是失控,是生命力。”
老人颤抖着坐下,老泪纵横。“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人头落地了。小荷死的时候,我就发誓,绝不让你们走她的老路。”
“我们也没想走。”小满蹲下身,握住他的手,“但我们也不能跪着活。小荷教我的最后一课,不是如何躲刀,而是如何在刀下种花。”
李公公久久无言,最终从怀中掏出一把铜匙,放在井沿上。
“这是通往礼部尚书私宅枯井地道的第三把钥匙。另外两把,一把在你手里,一把在沈知白那儿。我本想毁了它,可……我还是带来了。”
小满没有接。“留着吧。下次你若再动摇,就来这儿看看这口井。它埋过谎言,也映过月光。但它从未吞没过声音。”
春雷始鸣,万物复苏。一场悄无声息的清洗在内部完成。自此之后,再无文本被擅自改动。反而各地微光屋自发组织“校经会”,每季互相比对版本,确保传承纯正。
而“心灯节”的影响持续扩散。第二年,极北来信者再度传来消息:他们已在冰原上建起一座“铃塔”,高九丈,全由冻土与坚冰垒成,塔顶悬一口铜铃,风吹自动,声传十里。每逢心灯节,孩童们便环绕塔底齐唱:
>“风吹铃草蓝,
>火照人心寒。
>若问谁点灯?
>千家灯火都是咱。”
歌声穿越雪暴,竟被南下的驼队带回中原,一夜之间传遍市井。
就在这一年夏天,京城突发奇变。皇帝病重,太子监国。朝中权臣趁机推动“正俗令”,宣称要“肃清民间妄言,匡扶纲常伦理”,下令查封所有未经官府认证的讲学场所,首当其冲的,便是四千余处微光屋。
诏令下达当日,全国震动。
然而,预料中的镇压并未立即展开。因为就在次日凌晨,京城内外三百二十七口古井同时传出异响??井壁潮湿处浮现出墨迹,全是《守望录?外篇》节选,字迹清晰,宛如新写。更有甚者,某些井中打上来的水,竟带着淡淡墨香。
百姓惊疑,纷纷围观。有识字者高声朗读,立刻引发人群聚集。三日后,连大理寺门前的石狮口中也被发现塞着纸条,上书:
>“井可封,泉不竭;
>口可堵,声不止。
>微光不在屋,而在人心隅。”
监察御史上报朝廷,称此为“妖术惑众”。可民间传言四起,有人说这是“地脉显灵”,有人说是“亡魂执笔”,更有老僧断言:“此乃万民共念所化,心诚则字现。”
实际上,这是“燎原行动”中最隐秘的一环??“墨泉计划”。早在半年前,小满便命药师研制出一种遇湿显形的药墨,混入各地信使饮用的茶粉中。这些人常年奔波,体内积存药墨,排泄物渗入地下,经特定矿物催化,便会在潮湿岩壁上浮现文字。每人不过排出微量,但数千人联动,便成了“地下经脉”。
这一招,既无组织痕迹,又无法追责,更激发了民众的神秘信仰。
压力之下,太子不得不暂缓查封令,改为“限期登记”。谁知登记开始第一天,各地衙门前便排起长队。农夫牵牛而来,牛角上挂着铜铃;织女抱布而至,匹缎内绣满经文;就连乞丐也捧着破碗,碗底刻着“宁饿不伪”四字。
官员问:“你们这是做什么?”
答曰:“我们来登记‘微光屋’。”
“可你们没有房子啊。”
“有。”他们齐声说,“我们的心就是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