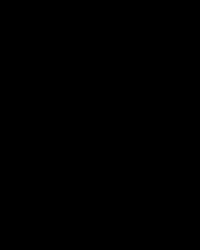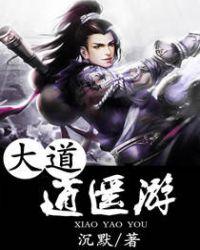宝书网>第一天骄 > 第六百六十七章 有胆你就来(第4页)
第六百六十七章 有胆你就来(第4页)
第十一年秋,联合国召开“情感文明峰会”。各国代表齐聚日内瓦,讨论是否应将“释怀教育”纳入基础课程体系。争议激烈,有人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有人则坚持:“一个不懂告别的民族,终将被执念压垮。”
会议陷入僵局时,主席台的大屏幕突然黑屏,随即跳出一段视频。
画面中,年幼的林知夏站在释怀亭前,面对镜头,认真地说:
“我妈妈告诉我,爱一个人,不是要把她锁在脑子里,而是让她活在我的选择里。”
“比如我现在每天多吃一口饭,因为她讨厌我饿肚子。”
“比如我学吹笛子,因为她喜欢音乐。”
“比如我来这里,因为她说,这里是‘心能呼吸的地方’。”
“所以,请你们也允许人们……好好地告别吧。”
全场寂静。
良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外交官起身,摘下领带,放入会场设置的“暂存箱”中。“这是我妻子结婚那天亲手系上的。”他说,“我一直舍不得换。但从今天起,我想试试轻松一点地活着。”
决议通过。
“释怀空间”正式成为人类文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多年后,当林知夏也成为白发老人,他常常坐在阿野曾经的位置上,教孩子们吹笛。
他依旧吹不好,每个音都歪歪扭扭,像是醉汉走路。可孩子们都喜欢听,因为他们说:“这样听起来,才像是真人在说话。”
某个清晨,他发现自己手腕内侧浮现出一行荧光文字,与当年阿野所见一模一样:
>“我学会了放手。
>所以我能回来。
>林知夏,谢谢你听见我。”
三秒后,字迹隐去。
他笑了笑,拿起陶笛,吹出一声刺耳的高音。
风起了。
花瓣飞扬。
而在宇宙深处,那艘无名探测舱仍在航行。舱壁铭牌新增了一行小字:
>“新增携带信息:关于如何优雅地开始。”
>“更新时间:今日。”
>“返航指令:永不更改。”
风,仍在吹。
你听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