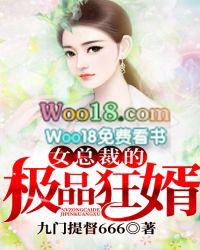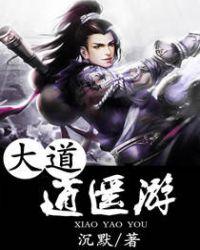宝书网>虎贲郎 > 第740章 大岘山西(第1页)
第740章 大岘山西(第1页)
大岘山的西侧,沂山余脉处。
孙策座下西极骏马剽捷善跑,骑从追赶不及。
他思索衡量之际任由坐骑发挥,等他回神时已在沂山余脉的一处山梁上。
山梁树木早已被樵夫砍伐,近些年也生长出一些灌木。。。
春雨淅沥,晋阳城外的麦田泛起新绿。赵明远拄着竹杖缓步走下思子台,脚边泥泞微湿,野草已悄然钻出地面。他停下脚步,望着远处一群孩童在田埂上追逐风筝,那是一只用旧书纸糊成的燕子,尾翼还写着半句《信义录》:“言不可废,如春不可阻。”
阿兰朵撑伞而来,将油布披风轻轻搭在他肩上。“你又去了碑林?”她问。
“三百零七座碑,每一块都该有一张脸。”赵明远低声道,“可我们连名字都找不全。有的只知姓氏,有的仅余乳名,还有一个孩子,死时不过十一岁,因在校场朗读《辛亥真相录》被押入狱,三日后‘暴病身亡’。他的母亲至今不知葬身何处。”
阿兰朵默然。良久,她轻声说:“林照儿昨夜来信,说成都信义塾的学生们正把那些无名者的事迹编成歌谣,教给山中村童。她说,只要有人唱,他们就还活着。”
赵明远点点头,目光投向南山深处。守心寨的旗幡仍在风中飘扬,但寨墙上已不见刀光剑影,取而代之的是晾晒的经卷与讲学图谱。十年前的烽火,如今化作书声琅琅。
然而平静之下,暗流未息。
三日前,一名西域商人自疏勒归来,在晋阳驿站猝然暴毙。尸检发现其腹中藏有蜡丸,内裹绢条,上书八字:“盟约将裂,烛龙北顾。”赫连曜闻讯即刻调兵巡边,并遣快马传书:近来多股商队遭劫,货物尽焚,唯独不取金银,专毁印有“信义”字样的文书与律典抄本。
“这不是盗匪。”赫连曜在信中写道,“是有人想让丝路断言。”
赵明远闭目良久,忽问身旁陈知微:“《监察之道》讲义可已誊清?”
“已成三卷。”陈知微恭敬答道,“末章题为‘权力之眼当向内照’,引用萧缜案、张让遗诏疑云及南中教案旧档,阐明监察若失其本,反为压迫之刃。”
“好。”赵明远睁开眼,“明日便发往各郡信义塾,另加一道附令:凡讲授此篇者,须组织学生走访本地衙门,记录百姓诉状,汇编成《民瘼实录》。”
陈知微一怔:“这……恐惹非议。”
“非议才是检验真理的炉火。”赵明远淡淡道,“我们推翻了以言定罪,却不等于天下皆敢直言。许多人仍怕官府,怕邻居告密,怕子孙受累。要让他们看见??说话不但无罪,还能改变现实。”
话音未落,门外传来急促马蹄声。一名年轻卫士飞奔而入,双手呈上一封火漆密函??来自敦煌。
信是莫高窟一位老僧所写。他说,月前有批朝廷特使抵达沙州,名义上督查佛经刊刻,实则强令僧人交出所有涉及“梁承业事件”的壁画底稿,并威胁若再供奉其画像,便以“私藏逆党”论处。
“但他们没想到。”老僧写道,“我们早将真迹摹于千佛洞最深处,且每一幅都留有题记:‘此非一人之冤,乃万民之镜’。更妙的是,已有三百六十名沙弥背下了整部《辛亥备忘录》,哪怕焚尽典籍,记忆仍在唇齿之间。”
赵明远看完,嘴角微扬,眼中却无笑意。
当晚,他在书院召集核心诸人议事。林照儿、赫连曜、阿兰朵、陈知微皆至,连久居南山养病的旧吏郑伯昭也乘舆而来。
“他们开始反扑了。”赵明远将敦煌信件置于案上,“不是刺杀,不是纵火,而是抹除记忆。比刀更狠的,是让人忘记曾流过的血。”
赫连曜冷笑:“那就让他们知道,西域不止有黄沙,还有不肯低头的脊梁。我即刻启程西行,召集十二部落首领,重开‘信义盟会’。既然他们怕真相流传,我们就让它传得更远??越过葱岭,直达波斯边境!”
“我也去。”阿兰朵忽然开口,“父亲的遗书里提过,龟兹王宫藏有一面‘回音铜镜’,据说是汉代使者所赠,能将一句话的声音留存百年。若真存在,我要亲自寻回。它不该只是古物,而应成为誓言的见证。”
赵明远看着她,良久方点头:“去吧。但切记,你们代表的不是复仇,而是传承。不要带兵压境,要用道理服人。若哪一族不愿加入,也不可强迫。信义若靠武力推行,便不再是信义。”
众人领命而去。唯有林照儿留下。
“你在担心什么?”她问。
赵明远望向窗外细雨。“我在想,当年崔胤为何不怕我们?因为他认定百姓愚昧,只要控制住文字与声音,就能掌控人心。可今天我们做到了他曾恐惧的一切??言论自由、平冤昭雪、百姓议政。但他错了,我们也可能正在犯同样的错。”
“怎么说?”
“我们太专注于制度建设,却忽略了人心的脆弱。”他缓缓道,“一个八岁孩童能在街头朗诵《信义颂》,这是希望;可同一个孩子,也可能因一句妄语被人唾弃。自由不只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更是每个人能否容忍异见的胸襟。倘若我们只许自己说真话,却不容他人质疑,那不过是换了主人的牢笼。”
林照儿沉思许久,忽道:“所以你要编《信义续编》?”
“正是。”赵明远取出一册手稿,“前三章已完成:《何谓宽容》《异议的价值》《权力如何腐化善念》。我希望下一代学子明白,信义不仅是对抗暴政的武器,更是日常生活中对弱者、对异己者的尊重。”
数日后,阿兰朵与赫连曜率轻骑出发,随行者仅有百人,皆为精通多语的学者与工匠。他们携带的不是兵器,而是拓印工具、律法译本与录音陶埙??一种能将人声封存于空腔陶器中的古老技艺。
沿途所至,民众夹道相迎。高昌长老以葡萄酿酒相敬,吐鲁番妇人献上绣有“双玉合璧”图案的头巾,就连曾经效忠北疆军阀的残部后裔,也在路口设香案跪拜,忏悔父辈罪行。
至龟兹王宫,新任摄政王妃亲自迎候。她年逾五旬,眉宇间仍有当年宫廷女子的风骨。她引众人入秘殿,揭开锦缎,露出一面青铜圆镜,直径三尺,背面镌刻飞天奏乐图,正面光可鉴人。
“此镜确能存声。”王妃道,“古法是以纯银镀面,辅以共振石匣。每逢重大誓约,君主在此前诵词,声波渗入铜质,百年后以特定频率敲击,仍可重现原音。”
阿兰朵上前,指尖轻触镜面,仿佛触摸父亲的灵魂。
当夜,她在宫中举行仪式,邀请西域七国使节共聚。她立于铜镜之前,朗声宣读《辛亥三号备忘录》全文,末了说道:“今日我以阿兰朵之名,将这段历史注入此镜。若有后人问起真相为何,便敲响此镜,听那穿越百年的呐喊。”
钟槌轻击,嗡鸣悠长,竟似有无数voices叠加其中??有囚徒的哀求,有刺客的冷笑,有母亲的哭泣,也有少年赵明远在雪夜里吹响的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