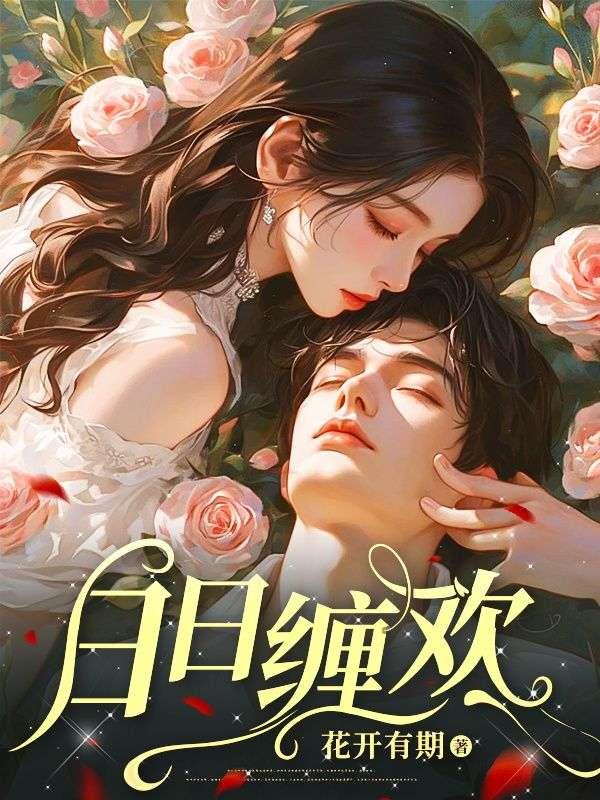宝书网>无声情话gl > 第24章(第2页)
第24章(第2页)
杨卿诗跑去房间里扯了两张纸,抱着妈妈的小腿,高高举着纸巾,嘴里发出‘啊啊’的嘶哑声,想给妈妈擦眼泪。
苏茗听到杨卿诗的声音,又哭了,冲着杨卿诗说:“你别啊了,你知道你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吗?”
话还没说完,苏茗就蹲下来抱着杨卿诗,埋在她的肩膀里大哭。
杨卿诗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哭,但她能感受到妈妈的难过,所以她也跟着难过,嘴一瘪,也开始哭。
母女俩的哭声让杨泽远厌烦,尤其是杨卿诗,每哭一声,就让他更恼怒一分。
“哭哭哭,哭个鬼啊!”他指着母女俩,“再哭就都给我滚出去!”
杨卿诗吓得不敢哭了,爸爸一向脾气不好,家里人都不敢招惹他。
那天,杨泽远和苏茗大吵了一架。
杨卿诗躲在房间里,听见了爸爸的那句:“你看你生的女儿,生了个废物,连话都不会说,她以后还有什么用?”
然后她听见了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接着是苏茗声嘶力竭地叫喊:“怎么就没用了?她以后怎么就没用了?还有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什么叫我生的女儿?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吗?你平时一天到晚不着家,不是在外面打牌就是在外面喝酒,你天天在外面跟你那些朋友吹嘘女儿多可爱多听话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现在女儿出事了,你又怪在我一个人身上……”
“老子在外面打牌喝酒是在挣钱!”杨泽远也摔了个东西,直接摔在卧室门上,吓得杨卿诗拿被子盖住脑袋。
“天天让你在家里面带孩子,让你教她,结果给她教成个哑巴,”杨泽远轻笑道,“也不知道他这情况是遗传的谁,反正不是我,我祖上三代都没有哑巴,你家里也没有,那就奇怪了,这到底是遗传的谁啊?”
他这话就是明晃晃的怀疑,眼神也变为质疑,“你他妈是不是背着老子在外面鬼混啊?”
苏茗的额角青筋暴起,气到嘴角抽搐,她竭力忍耐着怒火,说:“你再说一遍?”
杨泽远嗤笑一声,说:“被我说中了是吧?毕竟咱俩结婚之前,我可一直都在外面忙于工作,倒是你每天挺清闲的,没准你就是那个时候背着我跟别人搞在一起了,敢情我这么些年在帮别人养孩子。”
“杨泽远你个畜生!”
苏茗从小得到的教育便是礼义廉耻,家里人也都是高知分子,家训是洁身自好、恪守成规,才得以塑造出苏茗如今这温和有礼的性子。
但杨泽远这一番话,无疑是将苏茗的人格和自尊都踩在地上,碾个稀碎。
那一晚,杨卿诗在房间里,听着外面父母打架的动静,躲在被子里偷偷抹眼泪,她也不敢哭,怕哭了爸爸又要骂她了。
自那之后,杨卿诗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家里的幼儿教学玩具都被扔了,爸爸开始整日不回家,妈妈也学会了喝酒,只要喝了酒就抱着杨卿诗哭。
他们打架弄坏的家具一直没人来修,苏茗就在一片破烂家具里喝酒。
杨卿诗一直都不能明白,家里怎么就这样了,但她隐约察觉,是因为自己。
因为爸爸每次回来,都会把杨卿诗锁在房间里,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不想看见你。”
关的次数多了,杨卿诗一看见爸爸回来,就自觉回到房间锁上门,等爸爸走了再出来。
某一次,杨泽远也喝醉了,他朝杨卿诗招招手,让她过来。
杨卿诗很开心,以为今天不用被关房间了,跳着跑过去。
杨泽远捏住杨卿诗的手,捏的很用力,杨卿诗很痛,但她不敢把手抽出来,怕惹爸爸不高兴。
“宝贝,你叫一声爸爸。”杨泽远语气温柔,眼里带着期待。
杨卿诗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爸爸对她这么温柔的说话了,她很想按照爸爸的要求来,可是她无论怎么努力,依旧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嘶哑声。
杨泽远就在这难听的声音中渐渐失去耐心,他一把将杨卿诗踹到在地。
这一脚踢在肚子上,杨卿诗霎时疼得脸色煞白,犹如胃绞痛一样,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杨泽远并没有及时查看她的伤势,而是把她提起来,又扔进房间里,锁上门。
这一次,杨卿诗被关了四天。
头天晚上,她肚子疼的快要晕过去,不停地干呕。
接下来的四天,她断水断粮,被困在房间里,杨泽远没有回来,苏茗也没有,好像他们都忘了家里还有个人。
比饿肚子更痛苦的是恐惧,在一个十平米的房间里,一个人从早到晚,又从晚到早,她不敢睡觉,不敢闭眼睛,一到夜里,她就会躲进衣柜里,抱着妈妈的衣服寻求一丝安全感。
她哭了两天,本就沙哑的嗓子哭到最后完全发不出声音,再加上她没喝过一滴水,哭多了也哭不出眼泪。
四天后,苏茗在床底下找到了已经饿晕过去的杨卿诗,手里还抓着一卷卫生纸。
在医院治疗时,医生还从她的胃里找到了还未消化完的纸巾碎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