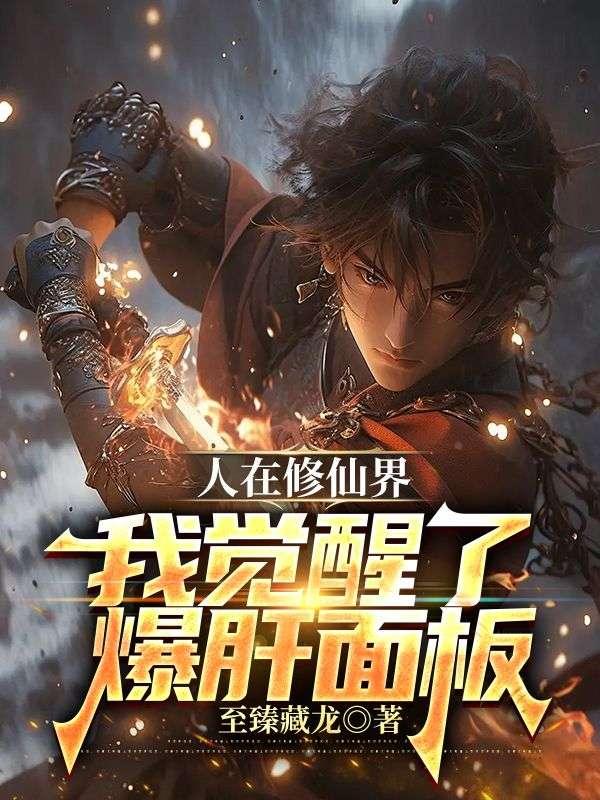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主母归来 > 100110(第4页)
100110(第4页)
如今,沈安宁这里的房子着了火,却烧得张绾亦随着坐立难安了起来。
话说张绾是沈安宁在京中最好的挚友,沈安宁虽对陆家早已毫不在意,在沈安宁的心目中,早在她搬离陆家的那一日,陆家早已同她桥归桥路归路了,而陆家那些腌臜过往每提及一次,对她来说都宛若活吞了一只蛆那般恶心,不过有人一同互诉心肠,总归是一件畅快的事情。
又想着张绾心性良善,而廉家亦绝非什么安乐窝,沈安宁便也不曾藏着掖着,只当作警示般,将陆家近来这一系列所为在张绾面前全部如实一一道来。
包括当日那陆安然是如何陷害陆绥安,又是如何想要登堂入室,再是如何传出有孕一事想要逼得她同意将她抬作平妻,再又是如何事迹败落,孩子又是如何离奇成为了陆靖行的,然后又是如何导致小房氏流产,她一字不落的淡定输出,满足了张绾所有的好奇心。
是的,沈安宁虽已搬离了陆家,可对陆家之事多少还是有些耳闻,她知道了陆安然被赶出陆家一事,亦知晓了那小房氏小产一事。
前者,她并不意外,小房氏有房氏护着,又有娘家撑腰,陆家自是不可能会像糊弄她那般,去糊弄小房氏,这个世界从来都是欺软怕硬,有着两幅嘴脸的。
沈安宁的讥讽比愤怒更多。
而听到后者时,沈安宁一度沉默了半刻钟时间之久。
这个消息着实有些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要知道前世小房氏可是生了一儿一女,她如今这肚子里怀的可是陆家的长孙,没想到就这样直接没了?
这算不算是煽动了蝴蝶的翅膀呢?
这一世,她改变了自己的运势,于是,陆安然肚子里的孩子从陆绥安的变成了陆靖行的,而受害者亦从她变成了房思燕。
虽自己避了这一祸,虽房思燕肚子里的那个没了的孩子,虽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却也多少令沈安宁有些唏嘘不已。
当然,她隐
去了陆绥安除夕夜归来那件事。
话说沈安宁张弛有度,娓娓道来,就跟茶楼里的说书先生似的,说得那叫一个引人入胜,只听得张绾时而皱眉,时而切齿,时而噌地一下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听到气愤之处,甚至一气之下径直摔碎了手中的玉盏。
“真是好不要脸,那陆家……那陆家怎养出了这样一个烂了心肝的娼货。”
“这同外头那些粉头娼妇又有何异?”
“若无陆家纵容,那养女怎有胆子干出这种腌臜事来?”
话说,听到这陆家这般种种倒行逆施的恶心之事后,张绾气得一度浑身发抖。
而听到那陆安然的真实身份后,张绾更是气得一度咬牙切齿,甚至一度气红了眼圈,冲着沈安宁浑身乱颤道:“那陆家是反了天了吧,这不是骑在人头上拉屎么?”
“简直欺人太甚,宁儿,他们陆家真是将你当软柿子捏,竟这般欺压羞辱人,臭不要脸,臭不要脸,简直……简直气煞我也。
话说,一整个上午张绾骂骂咧咧,只拉着沈安宁一道将那陆家祖宗十八代挨个问候了一遍,只将整个陆家骂得那叫一个狗血淋头。
饶是张绾自问经历不少,她们张家自捆绑到了皇家这条大船上后,整个家族万般不由己,随着这条大船的倾覆而倾覆,又随着这条大船的翻身而翻身,张绾的婚事一波三折,生生被拖到了二十岁大龄还未曾嫁人,后转眼之间又嫁到了廉家这样的权贵之家,她自问自己经历不少,见识不少,可却依然被陆家,被沈安宁的这桩桩曲折离奇的遭遇震碎了脑子。
只觉得陆家这一桩桩大戏,简直比说书先生嘴里的那些故事还要离谱糟心。
话说张绾久久缓不过神来。
而沈安宁是个体面人,摊上陆家这档子糟心事,她无人诉说,她如今诰命在身,又无宗族长辈撑腰,自是不会如同泼妇般跑到陆家大门前破口大骂,为自己出上一口恶气,亦没有向他人互诉衷肠的习惯,再者,便是有,亦无人诉说起,总不至于回到沈家,向郝氏,向牧哥儿,贵哥儿这帮小鬼抱怨吐槽吧。
故而,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只能自己默默承受,默默消化掉。
不想,一惯内秀的张绾竟在今日一改往日温婉柔雅的做派径直破口大骂了起来,她出口成章,甚至面目狰狞,恶语相向,听得沈安宁那叫一个目瞪口呆,吃惊哄笑不已,只哄笑过后,又莫名觉得畅快不已,只觉得酣畅淋漓的同时,那种被人维护,被人庇佑的感觉,让沈安宁触动不已。
于是,这日两人一道吐槽,一起怒骂,一道脱下鞋袜,围炉煮茶煮酒,悉数这一个月来,二人的各自过往经历,倒是难得酣畅快活。
说完,骂完,张绾终究还是忍不住一脸怜惜和关切的看着沈安宁道:“好在,那养女到底还是被赶了出去,宁儿,那往后,你该如何打算?”
说到这里,张绾仿佛觉得十分解气,然而还不待沈安宁回答,便又立马追问道:“沈家没派人过来接你回去?”
说着,便见张绾忽又立即咬紧牙关,冲她道:“即便事情弄清楚了,与那陆世子无关,但是陆家不分青红皂白在先,他们欺人在先,宁儿,听我的,此番定莫要这般轻易的回去了,你今日若这般轻飘飘的回去了,他们明日便只会越发肆无忌惮,全然不将你当回事,至少……至少也要等他陆绥安回京后,亲自用八抬大轿将你请回去,你才能回去,怎么地也得给他陆家一个下马威,不然还当咱们好欺负了。”
话说,张绾一脸苦口婆心的给沈安宁出谋划策着。
在张绾的认知里,陆家这些事情确实办得不地道,只是女子摊上了这些事情往往也只能自认倒霉,日子还是得照样过下去,不然,还能如何?
她们这些做他人妇的,往往也只能在有限的余地里据理力争一番,若能争到,便是额外的所得,倘若争不到,便是悲催的开始。
她从未想过还有其他可能。
却不想,她这话一出,却见对面沈安宁静静地端详她半晌,忽而冷不丁冲她开口道:“绾儿,实不相瞒,我打算同陆绥安和离。”
话说,沈安宁用最寻常的语气,冷不丁对张绾说出这样一番惊天动地的话语来。
她这番话说得太过突然,语不惊人死不休,却不想,就是这般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惊得张绾噌地一下骤然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张绾只瞪大双眼呆呆愣愣的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