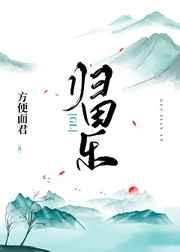宝书网>年代:大国崛起从工业开始 > 第454章 芯片进入纳米时代(第1页)
第454章 芯片进入纳米时代(第1页)
三天。
整整三天三夜。
白杨没有踏出过研究所办公室半步。
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隔绝了窗外的天光海色。
只有一盏绘图专用的无影灯,不知疲倦地投下稳定而明亮的光线,照亮了那张巨大的工作台。
工作台上,已经没有了那张画了一半的光刻机物镜组图纸。
取而代之的,是堆积如山的A4草稿纸和十几本摊开的专业书籍,从《金属材料学》到《流体力学》,再到《传热学原理》。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咖啡因和纸张混合的味道。
白杨的面前,摆放着最后一沓整理完毕的文件。
他将最后一页纸对齐,用订书机“咔哒”一声钉好,然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这口气息,仿佛将三天来的疲惫与紧绷,尽数吐尽。
他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片刻。
脑海中,那股庞杂如星海般的信息洪流,已经被他彻底梳理、消化,并转化为了这个时代的人能够理解和实践的技术文档。
系统灌输的知识,是完美的,是终极的。
但它就像一本天书,直接丢给现在的科研团队,他们多半会看得云里雾里,甚至会因为其中某些理论太过超前而产生怀疑,从而走上弯路。
白杨要做的,就是“翻译”。
他将那些超越时代的技术,拆解成一个个循序渐进的步骤。
他隐去了最核心、最颠覆性的理论,将其打包成一个个“黑箱”式的结论,然后围绕这些结论,设计出一条条清晰、明确、可执行的实验路径和工艺流程。
比如,关于“镓铟锡”这种常温液态金属合金的配方,他没有解释其内部复杂的微观电子作用机理,而是直接给出了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最终配比,以及对应的物理化学性质参数表。
再比如,关于液态金属在强磁场环境下的“磁流体动力学效应”,他略过了繁琐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推导,直接给出了几个关键的应用公式和经验常数,并标注了适用范围。
他就像一个站在未来,回望现在的引路人。
他不需要向登山者解释山顶的风景为何如此,他只需要在每一个岔路口,为他们竖起一块最清晰的路牌,告诉他们:走这边。
这三天的工作量,比他当初手绘一整套汽车图纸还要庞大。
因为汽车是“复刻”,而这一次,是“翻译”和“降维”。
他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站起身,走到窗边,“哗啦”一声拉开了厚重的窗帘。
午后灿烂的阳光,瞬间涌了进来,带着海风特有的咸腥和暖意。
白杨眯了眯眼,适应了一下久违的光亮。
窗外,是碧蓝如洗的天空,是椰林掩映下的红砖建筑群,远处,海天一色,几艘白色的帆影点缀其间,宁静而又充满了生机。
这便是他的研究所,也是他的王国。
“咚咚咚。”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请进。”白杨转过身,声音因为三天没有说话而略带沙哑。
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
他叫陈景明,是研究所材料科学部的负责人。
陈景明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实验服,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头发有些稀疏,但梳理得一丝不苟。
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常年和各种金属粉末、化学试剂打交道留下的,略显苍白的肤色,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透着一股子学者的严谨与执着。
“白所长,”陈景明看到白杨,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关切地问道,“您这是……又熬了好几天吧?这黑眼圈,都快赶上咱们上次攻关高温合金的时候了。”
白杨笑了笑,走到饮水机旁,给自己接了杯水,也给陈景明递了一杯。
“没办法,脑子里来了点新东西,不把它倒出来,睡不着觉。”他用一种半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陈景明闻言,眼神立刻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