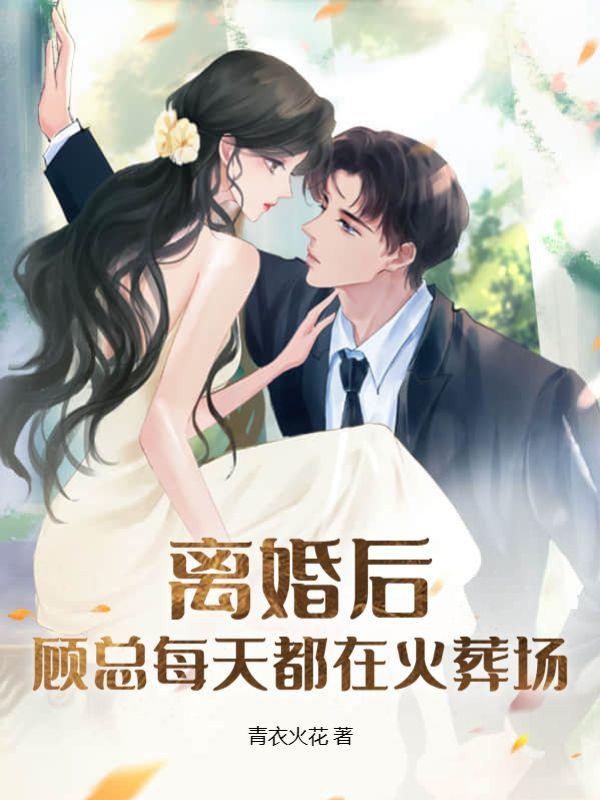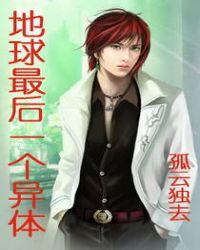宝书网>年代:大国崛起从工业开始 > 第371章 成功找到大型煤矿(第2页)
第371章 成功找到大型煤矿(第2页)
“明白!”小李用力点头,像打了鸡血一样,“我马上去办!”
看着小李风风火火离去的背影,白杨揉了揉太阳穴。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导演,费尽心机搭好了舞台,选好了演员,写好了剧本,现在,大幕终于拉开,演员们即将登场。
但他这个导演,却只能在幕后,紧张地盯着每一个环节,祈祷着演出能够顺利进行。
接下来的日子,果然如白杨所料,进入了一种高速运转但又充满程序性的节奏。
地矿部和煤炭部联合牵头,迅速成立了“晋西北及内蒙古东部煤炭资源潜力补充勘探领导小组”和相应的“前方勘探指挥部”及“技术专家组”。
文件以加急的形式下发,人员从各自系统内的王牌地质队和研究院所抽调,都是经验丰富、能打硬仗的骨干力量。
白杨的研究所,作为“理论策源地”,自然也被纳入了技术支撑体系。
白杨本人,被聘为“领导小组特邀技术顾问”,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头衔,既体现了对他的重视,又没有赋予他直接的行政指挥权,正好符合白杨低调参与、侧翼影响的策略。
各种协调会、技术对接会、前期准备会,密集地召开。
白杨带着小李等人,也成了这些会议的常客。
他需要不断地向不同层级、不同专业背景的人,解释他的“模型”和“推论”,回答各种刁钻或基础的问题。
每一次解释,他都小心翼翼,既要让对方听明白核心逻辑,又要避免泄露“天机”,把一切都归结于“基于现有资料的深度挖掘和综合分析”。
他甚至还主动指出了自己模型的一些“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比如对深部构造的推断精度有限,某些区域的古环境恢复存在多种可能解释等等。
这种坦诚,反而赢得了更多专业人士的信任。
搞技术的都明白,任何理论模型都有其适用范围和边界条件。
一个敢于承认自身局限性的模型,往往比一个宣称“包治百病”的模型更可靠。
与此同时,白杨也没闲着。
他利用自己“技术顾问”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获取了更多、更详细的地质资料。
包括一些过去他这个级别和单位接触不到的内部勘探报告和原始数据。
这些资料,进一步印证了他脑海中的“藏宝图”,也让他对即将开始的勘探工作,有了更强的信心。
他甚至还“建议”勘探队在某些区域,采用一些当时国内不太常用,但他知道非常有效的勘探技术组合,比如高分辨率地震勘探配合精密的重力、磁力测量,以及特定的钻探取样分析方法。
这些建议,都以“根据模型推断,该区域地质构造较为特殊,建议采用某某方法可能效果更佳”的形式提出,听起来合情合理,逻辑自洽。
日子就在这种紧张而有序的节奏中一天天过去。
初冬的寒风开始刮过四九城。
研究所的暖气还没来,办公室里有些阴冷。
白杨裹着一件军大衣,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浓茶。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是李副局长打来的。
“白杨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李副局长的声音带着难掩的兴奋,“刚刚收到前方指挥部的初步报告,晋西北那边,第一批补充勘探钻孔,有几个钻遇了厚煤层!初步判断,煤层稳定,厚度……相当可观!”
白杨的心脏猛地一跳,随即一股巨大的暖流涌遍全身。
他握着话筒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但声音却努力保持着平静:“太好了!李副局,这说明我们前期的推断方向是对的!”
“何止是对的!简直是神了!”李副局长显然非常激动,“王总工他们几个老专家,看了传真过来的钻孔柱状图,都说这次发现的意义,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
“周部长已经知道了,也非常高兴,让我一定转达他对你和研究所同志们的感谢和慰问!”
“这都是领导小组指挥有方,勘探队员们不畏艰辛、努力工作的结果。我们的理论,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白杨赶紧把功劳往外推,这种时候,越是成功,越要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