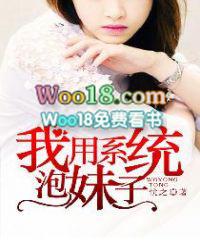宝书网>飞翔的梦想 > 第193章 边境迷雾(第1页)
第193章 边境迷雾(第1页)
秋分刚过,边境小镇的晨雾就浓得化不开。灯明踩着露水走进派出所时,值班室的老郑正对着一份报案记录发愁,搪瓷杯里的浓茶凉透了,茶渍在杯底结出深色的圈。
“又出什么事了?”灯明放下背包,胳膊上的旧伤在潮湿的天气里隐隐作痛——那是被严正明的人用钢管砸的,现在阴雨天还会发麻。
老郑指着报案记录叹气:“昨晚王家庄的李婶来报案,说她儿媳妇不见了。这是三个月里第五个了,都是外来的务工女性,失踪前都跟一个‘海外高薪招聘’的中介打过交道。”
灯明拿起记录册,失踪者的信息列得简单:姓名、年龄、籍贯,最后出现的地点都是镇上的“好运来中介所”。他注意到一个细节:五个失踪者都是二十到二十五岁,籍贯集中在云贵川的贫困山区,登记的“特长”一栏都写着“身体健康,无遗传病史”。
“这中介所查过吗?”
“查了,注册信息是假的,老板叫‘张哥’,没人知道真名,上个月就卷着钱跑了。”老郑递过一张传单,是中介所发的招聘广告,印着东南亚某工厂的照片,承诺“月薪过万,包吃包住,年底带薪休假”,末尾留的联系电话己经是空号。
灯明捏着传单走到院子里,晨雾中传来赶早集的吆喝声。这个边境小镇依河而建,对岸就是邻国,一条隐蔽的走私通道在雾里若隐若现。他想起三年前追查严正明的海外资金链时,警方曾打掉过一个利用这条通道运送实验器材的团伙,当时查获的货运单上,收货方正是东南亚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和严正明案里那家同名。
“李婶的儿媳妇最后在哪儿见的‘张哥’?”
“镇东头的废弃砖窑。”老郑指着雾蒙蒙的东方,“那地方邪乎得很,十年前烧砖时塌过窑,压死过三个人,后来就没人敢去了。”
砖窑的入口被半人高的杂草掩着,砖缝里钻出的野藤像干枯的手指。灯明拨开草堆往里走,脚踩在碎砖上发出咯吱声,惊得几只蝙蝠扑棱棱飞出窑顶。窑内弥漫着霉味和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让他瞬间想起严正明别墅地下室的味道,胃里一阵发紧。
在窑底的阴影里,他发现了一枚银色耳钉,上面镶着颗廉价的水钻。比对报案记录,是李婶儿媳妇的——她失踪前戴着同款耳钉。耳钉旁还有半截烟蒂,过滤嘴上留着淡淡的口红印,不是本地常见的牌子。
“有人在这里见过她们最后一面。”灯明用证物袋收好耳钉和烟蒂,手机突然震动,是刘畅发来的照片:东南亚某港口的监控截图,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正在指挥工人搬运集装箱,侧脸轮廓像极了严正明的前财务顾问。配文只有两个字:“小心。”
他刚把照片转发给冰如,就听见窑外传来脚步声。一个背着竹篓的老汉探头进来,看到灯明的警服,吓得手里的砍刀掉在地上,刀刃在雾里闪着光。
“我……我来砍柴的。”老汉结结巴巴地说,眼神躲闪着不敢看他。
灯明捡起砍刀,发现刀鞘上刻着个模糊的“明”字——是本地手工作坊的标记。“这附近有外人来过吗?比如口音不是本地的,或者开着外地牌照的车?”
老汉搓着手,半天才憋出一句:“前几天夜里,听见窑这边有汽车响,还看到……看到几个穿黑衣服的人,把一个大箱子抬上了车。”他突然捂住嘴,像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灯明心里一沉:“箱子多大?什么样的车?”
“黑颜色的面包车,没挂牌。箱子是木头条的,绑着铁链,看着挺沉……”老汉的声音越来越小,“警官,我啥也不知道,别问我了。”
看着老汉匆匆离去的背影,灯明突然想起严正明案里的一个细节:那些被运走的实验体,都是用带铁链的木箱装的。他拿出手机想给刘畅打电话,却发现信号被屏蔽了——这在信号本就微弱的边境小镇,太反常了。
回到派出所,冰如的信息发了过来:“烟蒂上的DNA比对到了,属于失踪者之一。耳钉内侧有微量的氯仿残留,她们是被迷晕后带走的。”后面附了张资金流向图,五个失踪者的银行账户在失踪前,都收到过一笔来自东南亚的汇款,金额不多不少,正好是“中介费”的数目。
“这不是招聘,是筛选。”灯明盯着资金流向图,手指点在东南亚的那个节点上,“他们用高薪做诱饵,筛选符合条件的女性,再用汇款记录确认她们的‘配合度’。”
正说着,老郑拿着一份协查通报跑进来:“市局刚发来的,邻省也丢了七个年轻女性,情况跟咱们这儿一模一样!”通报上附的监控截图里,中介所的“张哥”正和一个男人握手,那个男人的手腕上戴着块限量款手表——灯明在严正明的办公室见过同款,是他前财务顾问的私人物品。
雾渐渐散了,阳光穿透云层照在河面上,碎成一片金箔。灯明站在河边,看着对岸隐约的房屋轮廓,突然明白这不是简单的人口贩卖。严正明的基因实验需要“样本”,他的残余势力在延续这种罪恶,只是把“实验室”搬到了监管更松散的境外,把“实验体”换成了更容易得手的贫困女性。
他给刘畅打去电话,信号依旧时断时续:“这里的失踪案……可能和严正明的残余势力有关,他们在筛选‘基因样本’。”
电话那头的刘畅沉默了几秒,声音带着电流的杂音:“我马上申请跨省协作,你先稳住,别打草惊蛇。对了,老周也在边境做志愿者,他说有线索要当面给你。”
挂了电话,灯明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河面上漂着几片落叶,被暗流卷着往下游去,像那些被命运裹挟的失踪女性。他摸出兜里的旧照片——那是被拐三年的小男孩刚找回时拍的,孩子怯生生地拉着他的衣角,眼里却有光。
“放心,这次一定把她们都找回来。”他对着照片轻声说,仿佛在对所有等待救赎的人承诺。
下午,老周背着个磨破的帆布包出现在派出所门口,包里装着他整理的线索册。老人的手在翻页时不停颤抖,却在某一页停得格外稳:“你看这个,失踪的女孩里,有两个的母亲都得过同一种罕见病,这在基因上是有标记的。”
线索册上贴着剪报,是关于那种罕见病的报道,旁边用红笔写着:“严正明的实验日志里提过这种基因标记,说是‘理想样本’。”
灯明的后背瞬间沁出冷汗。原来所谓的“身体健康”不是指没有疾病,而是指携带某种“有价值”的基因缺陷。这些被精心筛选的女性,正在变成新的“实验体”,沿着严正明当年的罪恶之路,被送往境外的黑暗实验室。
夕阳西下时,灯明带着两名警员再次来到废弃砖窑。这次他们在窑壁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摄像头,内存卡里的录像显示,失踪女性都是被迷晕后,通过砖窑下的暗道运走的,暗道的出口首通河边的隐蔽码头。
录像的最后一段,是“张哥”对着镜头汇报:“第一批‘货’己上船,符合‘先生’的要求。他说……要多谢灯警官‘帮忙’清理了严正明的旧部,省了我们不少事。”
镜头转向码头,一艘伪装成渔船的货轮正在装货,甲板上隐约能看到几个蜷缩的身影。灯明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他们以为严正明伏法就是结束,却没想到黑暗早己顺着边境的缝隙蔓延,而这次的对手,比严正明更隐蔽,更懂得利用人性的弱点。
夜色渐浓,河面上的风带着水汽的凉意。灯明站在码头边,看着货轮消失在暮色里,拿出手机给刘畅发了条信息:“他们往公海去了,请求支援。”
远处的边境检查站亮起了警灯,红蓝交替的光芒映在河面上,像一道撕开黑暗的裂缝。灯明知道,这场新的较量才刚刚开始,而这一次,他们要守护的,不仅是正义,更是每个普通人不被当作“样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