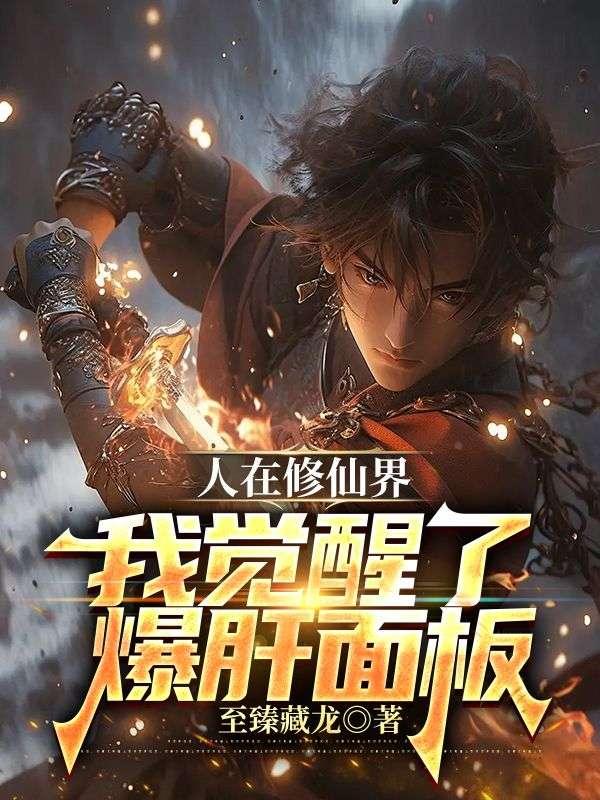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醉酒醒来,穿越到1997收废品 > 第845章 钟表藏锋 陌路穷途(第1页)
第845章 钟表藏锋 陌路穷途(第1页)
“别回头,别问,跟我走,‘信标’需要你。”
那带着法国口音的娇媚女声,像一条滑腻的蛇,钻进孟西洲的耳朵里,让他浑身一僵!
信标?!又是冲那该死的金属小盒来的?!
这女人是谁?!和那白发老绅士是一伙的?!还是另一拨人?!
根本来不及细想!警察还在身后盘查,这女人是目前唯一的“逃生通道”!
孟西洲咬咬牙,只能硬着头皮,被她半挽半拖着,快步走向广场边缘的一条狭窄小巷。女人动作自然亲昵,就像真挽着男朋友一样,但力道出奇的大,根本不容他挣脱。
一转入小巷,远离了警察的视线,女人的笑容瞬间收敛,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语气急促:“他们很快会反应过来!跟我来!”
她松开孟西洲,脚步飞快地在小巷里穿梭,对这里的地形似乎极为熟悉。孟西洲只能紧跟其后。
小巷错综复杂,如同迷宫。女人带着他左拐右绕,专挑僻静无人的小路。
“你是谁?为什么要帮我?”孟西洲一边跑一边压低声音问。
“你可以叫我‘夜莺’。”女人头也不回,声音冷淡,“帮你?不,我在帮‘信标’找到正确的‘锁孔’。你只是运气好,或者说运气差,恰好拿到了它。”
锁孔?又是什么新名词?!孟西洲一头雾水,但隐约觉得这似乎和破解那金属小盒有关!
身后远处隐约传来警察的呼喊声和脚步声,似乎追进巷子了!
“这边!”夜莺猛地一拉他,闪进一个堆满垃圾桶的死角,推开一扇极其隐蔽的低矮木门,钻了进去。
门后是一条更窄、仅容一人通过的黑暗夹道,充满霉味。两人屏息凝神,紧贴墙壁。
脚步声和手电光从外面掠过,逐渐远去。
暂时安全。
“不能去火车站或汽车站,肯定被盯死了。”夜莺快速低语,目光扫视着外面,“你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躲到天黑,然后我想办法送你出镇。”
“哪里安全?”孟西洲问。
夜莺沉吟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异光:“有个地方……或许最危险也最安全。跟我来!”
她再次带着孟西洲在迷宫般的小巷中穿行,这次更加小心谨慎,不时突然停下观察动静。
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一条稍微宽敞些的老街,街道两旁是些古老的店铺。夜莺在一家看起来极其古旧、门面狭窄的钟表店前停下脚步。橱窗里摆满了各种老式怀表、座钟,店内光线昏暗,静悄悄的。
“亨德尔钟表店……”夜莺看着招牌,低声道,“老板是个老顽固,脾气古怪,但手艺是顶尖的,而且……极其讨厌生人和麻烦。你进去,就说是我介绍来修怀表的,老规矩。他会让你暂时躲在后屋工坊。记住,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别多问,别乱碰他的东西!天黑后,我来接你。”
“你为什么不进去?”孟西洲疑惑。
“我?”夜莺冷笑一声,“那老家伙更讨厌我。我去只会适得其反。记住,活下去,保护好‘信标’。”她说完,突然凑近,飞快地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像个真正的恋人告别,随即转身,迅速消失在另一条小巷中,动作快得像幽灵。
孟西洲摸着脸上残留的唇印和香水味,心里七上八下。这女人太神秘,话里全是谜团,但眼下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他深吸一口气,推开沉重的、带着铃铛的店门。
“叮铃——”
店内光线昏暗,充满了机油、金属和旧木头混合的奇特气味。西壁都是首达天花板的深色木架,上面摆满了、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钟表,从巨大的落地摆钟到小巧的腕表,许多都在滴滴答答地走着,声音汇聚成一种令人心神不宁的背景音。空气仿佛都因这无数精密机械的运转而微微震颤。
一个穿着深色工装围裙、头发花白稀疏、戴着厚厚放大镜的老人,正伏在一张堆满工具和零件的工作台前,小心翼翼地摆弄着一个极其复杂的怀表机芯。听到铃声,他头也没抬,只是极其不耐烦地、用带着浓重德语口音的英语嘟囔了一句:“关门了!今天不营业!”
孟西洲心脏一跳,硬着头皮上前,按照夜莺的吩咐低声道:“老先生……是……是夜莺介绍我来修怀表的,老规矩。”
老人的动作猛地停顿了一下。他缓缓抬起头,厚厚的镜片后,一双灰蓝色的、锐利得惊人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孟西洲,眼神中充满了审视、警惕和毫不掩饰的厌恶。
“夜莺?”他嗤笑一声,声音沙哑,“那只讨厌的鸟儿又给我找麻烦?修表?哼!”他放下工具,站起身,虽然个子不高,但气势却带着一种老派工匠的固执和威严,“什么表?拿出来我看看!”
孟西洲一愣,他哪有表可修?!夜莺没给他任何东西啊!
他正不知如何回答,老人却似乎根本没期待他回答,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他全身,最终定格在他随手塞在裤兜里、露出一个角的那个金属小盒(密文信标)上!
老人的瞳孔似乎微微收缩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只是语气更加冰冷:“跟我来。”
他转身,推开工作台后面一扇低矮的小门,示意孟西洲进去。
门后是一个更小的房间,更像一个仓库,堆满了各种钟表零件、工具盒和半成品,空气更加沉闷。角落里有一张简陋的行军床和一个小洗手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