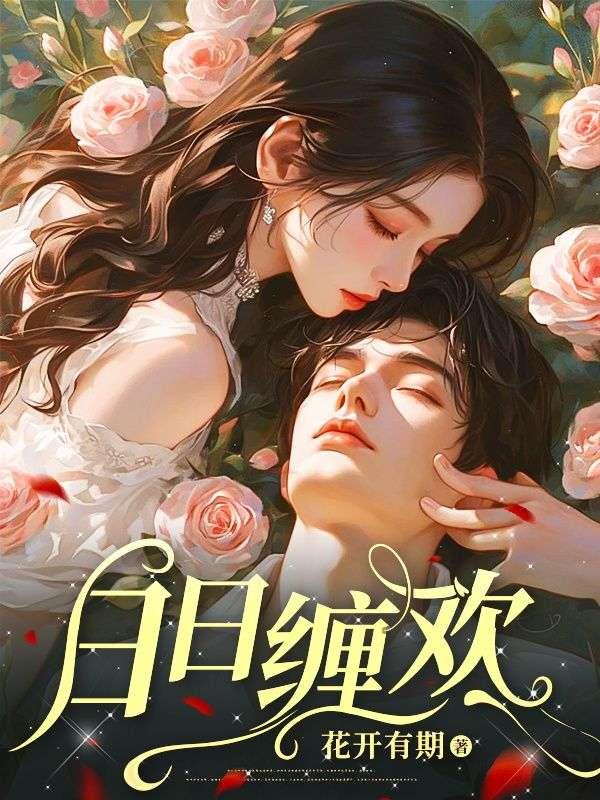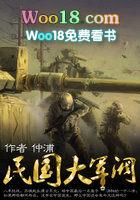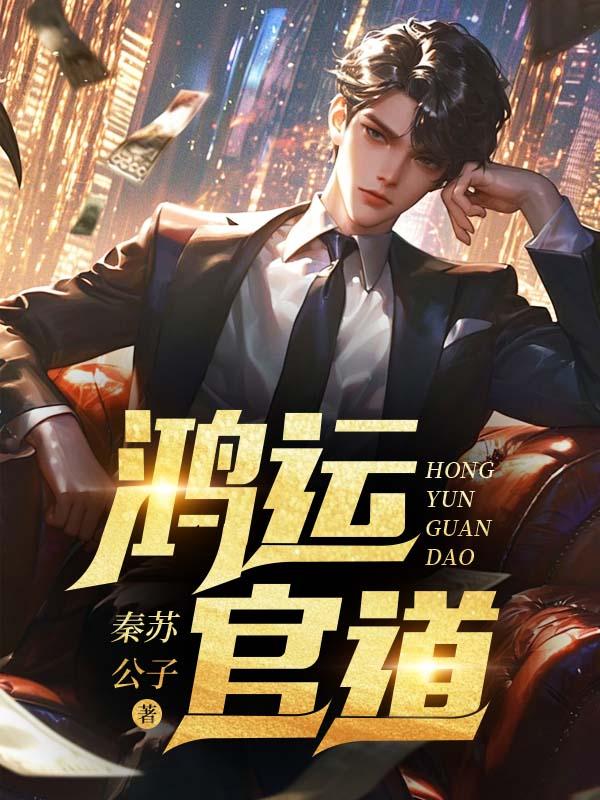宝书网>红楼:我是贾琏 > 第662章 没一个简单的(第3页)
第662章 没一个简单的(第3页)
方白衣能在太上皇年间坐稳首辅的位子,靠的就是他对官员的庇护,能救一个算一个,这才导致他威望极高。方白衣做首辅后,太上皇也没再杀一个大臣,除非是谋逆。太子案所谓的从逆者,方白衣的坚持之下,也仅仅是流放。
从这点看,周帝国也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其中以朱祁镇杀于谦为最。皇帝连于谦都杀,导致君臣离心离德的后果太严重了。
文臣也一样,党争失败的下场很惨,对政敌自然是穷追猛打,不死不休。
当然了,党争主要原因还是生产力发展停滞了,蛋糕不够分了造成的。这点看看现在的米国就知道了。
太平年间,一旦陷入了这种因为存量竞争的时期,党争注定是要出现的,为了利益斗的你死我活。晚唐如此,晚明也如此。
宋朝的党争也很激烈,但是皇帝少杀甚至不杀大臣,这才能在北宋倾覆之后,南宋半壁江山快速的凝聚成型,又坚持了一百多年。
明朝作为后世皇帝的反面教材,很大程度上与朱祁镇杀于谦,崇祯动不动就杀大臣有很大的关系。
君臣之间的信任被打破的后果很严重的,皇帝还喜欢杀大臣,那就完蛋的更快了,可以说一泻千里。
当然这些与贾琏没关系,他不是不想杀,而是不希望朝局动荡,影响了正在快速做大的蛋糕。
实际上研发厅、铁路局能存在,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现在是做大蛋糕的期间,没有必要为了存量利益斗的你死我活。
至于贾琏自身的遇刺案,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贾琏也看出来了,这不是哪一方能自己做到的,而是多方的合力所致。
原因也很简单,利益太大了,大到有的人愿意铤而走险。
至于皇后的王氏族人嘛,估计就是被人利用的蠢货。他们最多就是提供了帮助,王氏不可能拿出那么多死士,底蕴太浅了。
所以呢,李元表示有针对刺杀案的因素,贾琏心里也就是一笑而过。
真正想贾琏死的人,一定是资本同行,在资本增值的本能驱动下铤而走险,这才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
想到这里,贾琏没想过立刻进行激烈的报复,首先想到的是要加快股市的融资行动了,将更多的民间资本吸纳进来,缓解资本因为增值需求的焦虑。只要钱进了股市,那就不是他们能说的算的事情了。现在不着急,等缺钱用的时候,才是给这些人一些来自资本的教训的时候。
当然贾琏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对王氏出手,不就是为了打草惊蛇么?
内阁做出的流放关外的决定,李元一点想法都没有,全都快速通过了,就要求一个速度,别耽误过年。
至于废后的想法,李元还是按下去了。适当的敲打一下王氏,再拿下老牌王爷忠顺王,足以在短期内震慑皇亲国戚们,让他们别搞事情。
离开皇宫时已经下班了,贾琏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城南。
范平这边还在忙碌,看见贾琏进来,立刻上前汇报:“表面上看起来,皇亲国戚以及勋贵是倒贾的主要动力,因为他们吃相最难看,最粗糙。实际上倒贾成功,他们能吃的都是明面上的一些东西,负责造血的整个产业链,将落日晋商、徽商、两江豪商、闽浙商团之手。其中两江有相应的产业链,能够快速接收,其他商团,则有充足资本和现成的渠道来消化整个产业链衍生的利益。”
贾琏坐在靠在椅子上,轻轻的摇晃身子,自言自语:“有点多啊。”
范平冷笑道:“人手应该来自晋商为首的西北豪商群体,两江的商团相对松散,难以形成合力。他们提供的是官方的力量。只要大人出事,他们负责压下来,或者是在不伤及各方的前提下,将事情混过去。”
贾琏不动声色的问一句:“你想怎么做?”
范平正要回答时,柱子敲门进来道:“二爷,人到了。”
贾琏起身道:“就来。”走之前拍拍范平的肩膀:“报复是必须的,但不要留下任何收尾,想好再说,不要落下任何文字。”
隔壁的一个单独小院内,便衣的夏刚正在自斟自饮,一点都不带客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