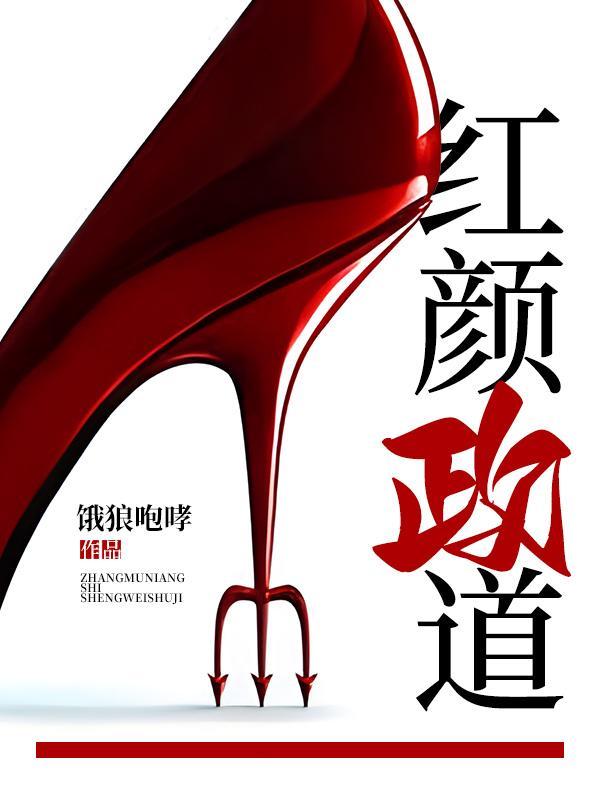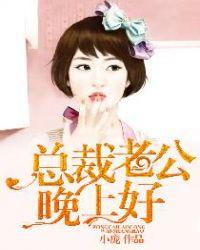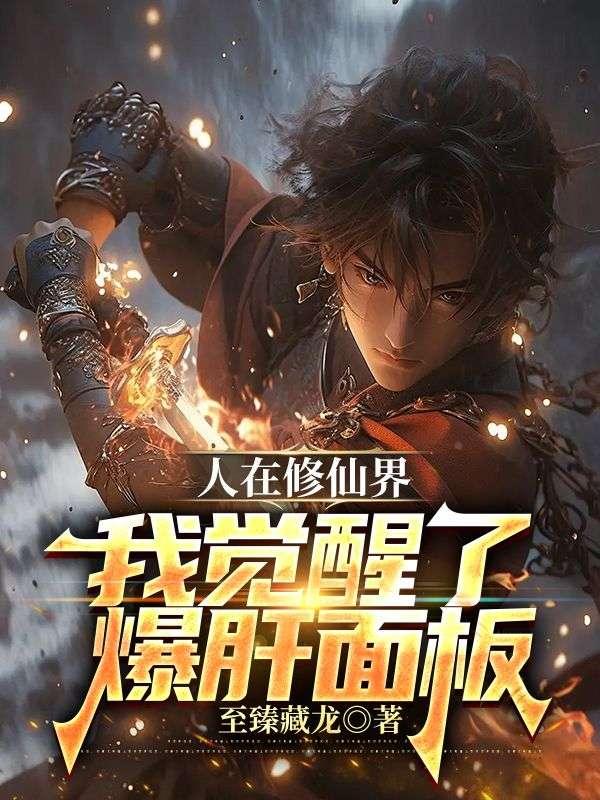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晋末芳华 > 第五百一十五章 出身差别(第3页)
第五百一十五章 出身差别(第3页)
“那就给它。”陈默戴上特制声波传导耳机,深吸一口气,开始吟唱。
不是《安魂》,也不是《土谣》,而是他自己编的一段旋律??简单、粗糙,甚至有些跑调,却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林奈随即加入,用口哨补全高音;周砚舟敲击舱壁打出节奏;阿依古丽以喉音营造回响;沈师傅则以杖击地,踏出古老节拍。
五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不成章法,却充满生命力。
音核剧烈震动起来。
水晶腔内迸发出璀璨蓝光,随即扩散成一张巨大的声场网络,覆盖方圆数十公里。海底沉积物纷纷扬起,形成螺旋状尘柱,宛如龙卷升腾。远处鱼群受感召般聚拢,围绕祭坛游成同心圆阵列。
突然,音核核心裂开一道缝隙,从中缓缓飘出一颗更小的金属球,通体透明,内部似有液态光流动。
“分核?”周砚舟惊呼。
“传承。”沈师傅热泪盈眶,“它要把火种传下去了。”
那颗新生音核缓缓上升,穿透海水,冲破洋流,最终破开海面,化作一道银色流星,射向夜空。
一秒,两秒……
全球十三个听钟节点同时警报响起:新信号抵达!频率未知,波形复杂,蕴含的信息量远超以往任何一段。
科学家试图解码,却发现传统算法完全失效。唯有当一名小女孩在云南用竹笛随意吹出几个音符时,服务器竟自动完成了九成以上的破译。
结果显示:这是一份地图。
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坐标图,而是一张“心灵共鸣热力图”??标记着世界各地尚未被发现的潜在听钟遗址,总数超过三百处。每一处,都对应一段失落的旋律、一种濒危的语言、一首即将消亡的民谣。
“它们还在。”林奈看着屏幕,声音哽咽,“那些声音……从来就没死。”
陈默默默打开日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下:
**“我们原以为自己在寻找过去,其实是在唤醒未来。”**
雨又下了起来。
这一次,没有人躲进屋檐。
他们站在听钟台中央,任雨水打湿衣衫,齐声唱起那首还未定名的新曲。歌声混着雷声,在山谷间来回激荡。
而在遥远的北极冰原,在寂静的撒哈拉沙丘,在亚马逊雨林深处,在喜马拉雅雪峰之巅……一个个模糊的身影也同时抬起头,仿佛听见了什么。
有些人拿起骨笛,有些人敲响皮鼓,有些人张口吟诵古老祷词。
他们互不相识,语言不通,文化迥异。
但他们唱的,是同一段旋律的碎片。
大地深处,那口沉睡已久的巨钟,终于轻轻颤了一下。
第一声,尚在酝酿。
但回响,已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