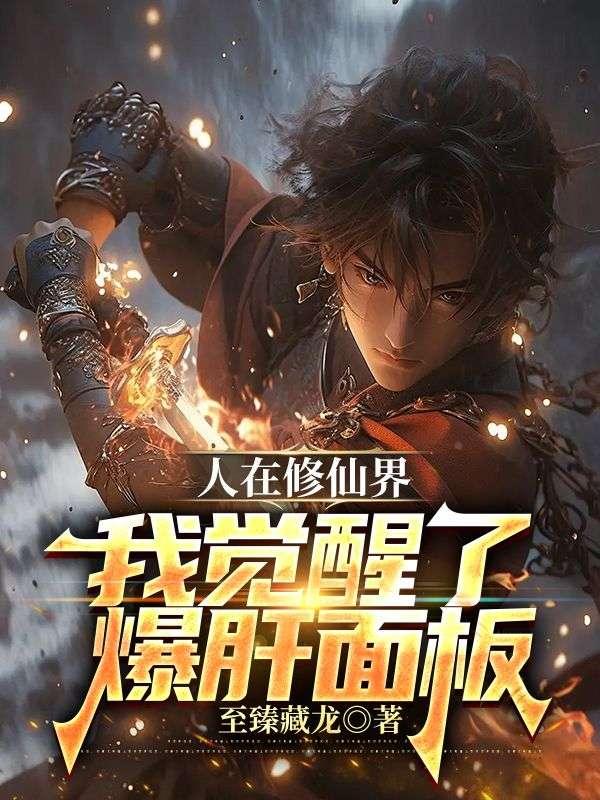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晋末芳华 > 第五百一十四章 心生猜疑(第2页)
第五百一十四章 心生猜疑(第2页)
“如果有人来问起我们去了哪里,”他说,“就把这台机器打开,让他们听一听里面录着的声音。”
“然后呢?”
“然后告诉他们:钟声从不曾消失,它只是换了地方响起。”
深海之下,光线渐隐。潜水器穿过层层暗流,抵达预定坐标。声呐显示,seabed上矗立着一组巨大石构,形似宫殿,顶部坍塌,珊瑚覆满,唯有中央一座圆形祭坛完好无损。坛心嵌着一块椭圆形黑石,表面光滑如镜,内部似有流光游动。
阿依古丽操控机械臂缓缓靠近。当探灯照亮黑石瞬间,所有人屏住呼吸??
那不是石头,而是一颗悬浮在水晶腔内的金属球体,直径约二十厘米,通体银灰,表面布满细密纹路,宛如指纹。更惊人的是,它正以极轻微的幅度脉动,每三秒一次,频率精准锁定在7。83Hz。
“和听钟台的共振频率一致!”林奈颤抖着记录数据,“它……在呼吸。”
周砚舟对照古籍残卷:“《泉州乐志》有载:‘音核者,纳百声之精,聚一心之诚,炼于雷火,藏于海渊。遇知音则鸣,非强取可得。’”
“怎么唤醒它?”阿依古丽问。
沈师傅闭目良久,忽然开口:“用‘心音’。”
他取出乌木杖,轻轻敲击潜水器舱壁,三下短,两下长,再三下短??正是《安魂》的起始节奏。随即,他开始哼唱,没有歌词,只有纯粹的音高起伏,如同母亲哄睡婴儿的呢喃。
一秒,两秒……
毫无反应。
正当众人失望之际,陈默忽然摘下通讯耳机,贴在唇边,轻声说:“小满,我们来了。”
这句话,他用了最平常的语气,像问候老友。
刹那间,海底震动。
那颗音核缓缓升起,脱离水晶腔,悬停于祭坛上方。表面纹路亮起幽蓝光芒,一圈圈声波扩散开来,竟使海水形成肉眼可见的同心圆涟漪。紧接着,一段旋律自核心传出??非电子,非机械,而是某种介于生物与矿物之间的发声方式,温暖而古老。
林奈泪流满面:“这是……《土谣》的变奏版,加入了南音的润腔技巧,还有马来甘美兰的金属震音……它是活的!”
音核缓缓旋转,光芒愈盛。突然,它分裂成十二道光束,射向海底不同方向。数分钟后,全球十三个听钟节点同时接收到一段新信号??一段全新的旋律,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仿佛来自未来的回响。
科学家称其为“第零律”,因它先于三律存在,却又包容三律。
哲学家称之为“初始之音”,认为它是人类集体潜意识中最原始的和谐原型。
而在云南怒江的村落里,一个五岁女孩在梦中醒来,拿起竹笛,吹出了这首曲子的第一个音符。她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吹,只说:“有个姐姐在我耳边唱了一句,我就记住了。”
消息传回听钟台时,已是春末。
陈默站在屋檐下,看雨又一次落下。这一次,他不再闭眼,而是仰头迎向天空,任雨水打湿脸庞。
林奈走来,递给他一杯热茶。“你觉得,我们算是完成了使命吗?”
他笑了笑:“使命从来不存在。我们只是恰好走到了这条路上,听见了一些声音,然后选择相信它们有意义。”
远处,孩子们又开始唱歌。这次不是《土谣》,而是那首从海底传来的“第零律”。他们唱得不准,节奏混乱,却无比真诚。
陈默忽然明白,昭华为何要将三律托付给普通人,而非帝王将相。因为真正的音乐,从不在完美之中,而在破碎处重生;不在掌控之下,而在放手之后。
他掏出怀中那张泛黄照片,再次凝视钟楼前的模糊背影。这一次,他不再疑惑。
他知道,那人是谁。
也许是他,也许是她,也许是你,也许是我。
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钟声就会一直响下去。
雨渐渐小了。
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斜照下来,正好落在听钟台中央的石碑上。那是他们后来立的,上面没有名字,只刻着一行小字:
**“此处曾有人,认真听过世界。”**
风起,铃响,歌声不绝。
大地深处,某处未被发现的共鸣井里,又一声低鸣悄然响起,像是回应,又像是召唤。
新的循环,正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