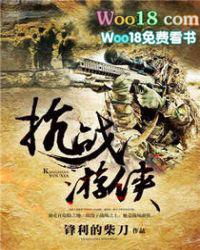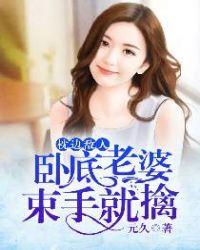宝书网>晋末芳华 > 第五百零八章 各司其职(第3页)
第五百零八章 各司其职(第3页)
次日清晨,他收拾行装,留下一封信给村委会。信中只有一行字:“我去追她的路了。”
他没有选择现代交通,而是徒步出发,沿着当年小满南下的轨迹,穿越云贵高原,进入横断山脉。一路上,他不再记录数据,也不接受采访,只是观察、倾听、感受。他在藏族寺庙听喇嘛诵经时察觉到声波与地磁的微妙共振;在彝族火塘边听老人讲故事时,发现火焰跳动的节奏竟与《月光谣》节拍完全一致;在一处废弃驿站遗址,他捡到半块破碎陶铃,摇晃时发出的音高,恰好填补了钟声缺失的那个音符。
三个月后,他在澜沧江畔的一座小镇停下脚步。
这里没有“耳语社”,也没有觉醒点标记,但每当夜深人静,居民都说能听见“水里唱歌”。陈默租下一间临江小屋,每日傍晚坐在岸边,任江风吹拂耳际。第七天夜里,他忽然感到左耳一阵刺痛,随即涌入一股奇异的听觉??不再是单纯的声音,而是一种混合了气味、温度、情绪的“全息感知”。
他“听”到了百年前一艘沉船的哀鸣,
“听”到了一对恋人在此诀别的誓言,
“听”到了某个孩子未来某日将在此处写下第一首诗的心跳……
他知道,这是“初音能力”的觉醒征兆。
就在此时,一封来自边境检查站的电报送到了他手中。
内容简短:
>“一名女子于昨日越过国境线,身份不明。她未持护照,但边防犬见到她后伏地不起。据目击者称,她口中哼着一首童谣,随行的十几名少数民族儿童自发跟随,声称‘她是我们的声音’。现已暂时安置于芒市接待站,请速确认。”
陈默看完,笑了。
他立刻启程,日夜兼程赶往芒市。
当他推开接待站铁门时,阳光正斜斜洒进院子。一个身影背对着他坐在石阶上,衣衫褴褛,发丝斑白,脚上的鞋早已磨穿。
但她轻轻晃动的肩膀,泄露了正在哼唱的旋律。
那是《月光谣》,带着云南山歌的尾音拐弯。
陈默站在门口,没有喊她名字,也没有上前。
他只是缓缓蹲下身,将右耳贴近地面,像多年前那个雨夜一样,静静地听着。
片刻后,大地传来回应??
先是遥远的一声钟鸣,
接着是十三个方向传来的震动,
最后,是脚下泥土中缓缓浮现的节奏,
如同心跳,如同呼吸,如同千万人同时开口,却又万籁俱寂。
小满停下歌声,慢慢转过头。
两人目光相接,没有言语。
但他们都知道,这一刻,世界又一次完成了共振。
风从南方吹来,穿过山谷、河流、森林与城市,携带着未尽的旋律,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