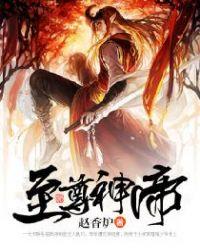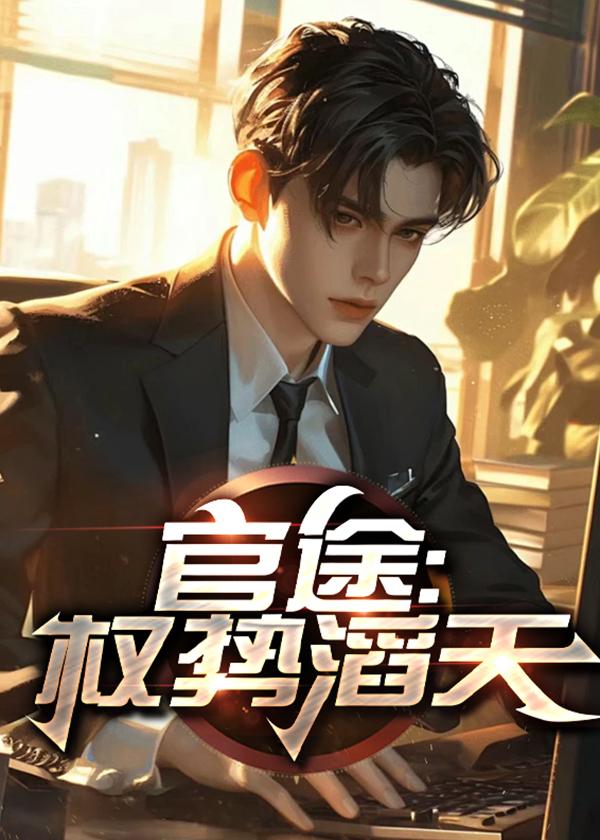宝书网>李兆廷综武:我家娘子是状元免费阅读全文 > 第565章 天剑VS佛心VS战神(第1页)
第565章 天剑VS佛心VS战神(第1页)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李白的《侠客行》有二十四句,侠客岛的石室有二十四间,前二十二间各刻录一。。。
暴雨倾盆,砸在终南山顶的祭坛石阶上,溅起一片片白雾般的水花。
老妇人手中的纸灯笼早已熄灭,但她仍紧紧攥着那根竹骨,仿佛那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唯一绳索。
她跪坐在火堆前,任雨水顺着皱纹沟壑流淌,口中喃喃:“老师……我讲完了。”
话音落下的刹那,火堆中忽然腾起一道青焰,不随风倒,反而逆流而上,在空中盘旋成螺旋之形。
紧接着,整座山巅的“鸣心lantern”
塔群同时震颤,七十二道光柱破云而出,交织于天心,竟在厚重雨云间撕开一个巨大的漩涡眼。
月光自缝隙洒下,照在祭坛中央那块晶石残片之上。
它动了。
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移动,而是内部那缕金色脉络骤然扩张,如血管爆裂般蔓延至整个表面,随即渗入地底。
一股无形波动以终南为原点,向九州辐射而去??比声音更快,比电光更静,所过之处,所有正在书写、讲述、回忆真实的人,都猛地一怔。
他们听见了。
不是耳朵听见,是骨头在共鸣,血液在低语。
一段旋律,极远又极近,像是从母亲子宫里带来的胎音,又像临终时耳边最后一声叹息。
那是《归烬谣》的变调,少了悲怆,多了抚慰;不再是控诉命运的呐喊,而是唤醒沉睡者的摇篮曲。
江南执灯塾内,三十七名学生齐刷刷抬头。
女讲师手中的粉笔“啪”
地折断,她瞳孔微缩,嘴唇轻启:“他在……召唤我们。”
不只是她。
岭南讲学堂里,正抄写梦境记录的学生笔尖顿住,墨迹晕染成一朵金花形状;川蜀安置点那位写下“阿禾”
的老妇人突然站起身,推开屋门走向雨中;北方边境雁门关外,一名守夜士兵放下长枪,从怀中掏出一支锈迹斑斑的音笛,颤抖着吹出第一个音符。
没有命令,没有组织,千百个曾被“忆梦籽”
侵蚀过灵魂的人,几乎在同一时刻做出了相同的选择:闭眼,深呼吸,然后开始说话。
“我记得……”
“我记得父亲死前握着我的手说‘别怕黑’。”
“我记得六岁那年发高烧,娘整夜用冷水浸布擦我额头,天亮时她倒在床边。”
“我记得第一次杀人那天,月亮是红的。”
一句句真实的话语如同雨滴落入湖面,涟漪层层叠加。
而在地下深处,那些埋藏已久的安魂坛遗址开始苏醒。
青铜匕首上的锈迹剥落,露出底下铭刻的古老文字:“以血为引,以忆为灯。”
尘封百年的地脉网络重新接通,每一条经络都因千万人的记忆共振而搏动起来。
林晚照站在观测台最顶端,浑身湿透,手中晶石碎片已化作一团温润金光悬浮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