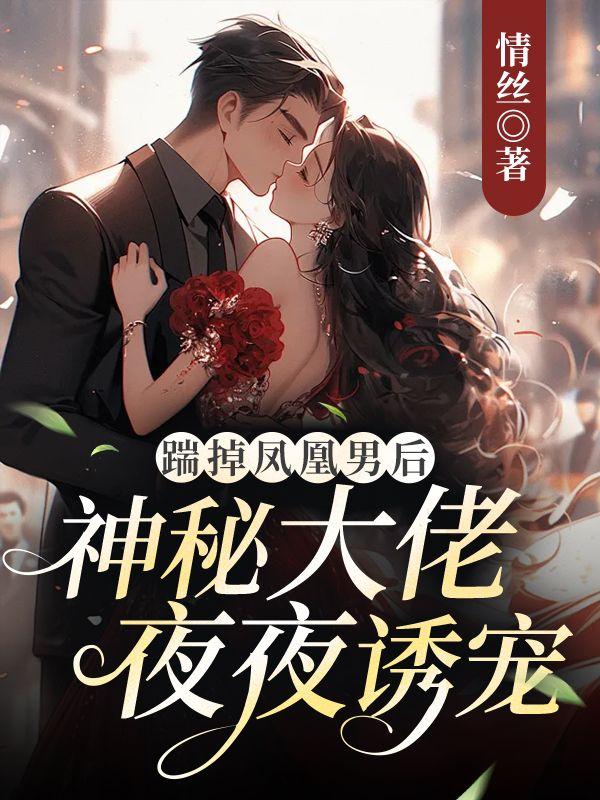宝书网>综武:我家娘子是状元李兆廷百度云完整版TXT > 第564章 数值怪偏偏觉得自己很有操作(第2页)
第564章 数值怪偏偏觉得自己很有操作(第2页)
植物学家取样检测后确认,其细胞结构中嵌入了一种未知能量波段,与“鸣心lantern”
塔释放的频率完全一致。
而每当月圆之夜,这些树木的年轮便会浮现细小文字,内容各异,却都指向同一个主题:**“我选择了记得。”
**
这一切,并非偶然。
林晚照站在终南山观测台上,手中握着一块刚从地下挖出的晶石碎片。
它原本是“愿种”
核心的残余,本应彻底湮灭,可如今内部竟浮现出一丝丝金色脉络,如同血管般搏动。
她的助手低声汇报:“第七次共振实验成功了。
全国七十二座lantern塔已形成闭环网络,新型‘忆真孢子’开始自然生成。”
“不是我们做的。”
林晚照喃喃道,“是他在做。”
她闭上眼,耳边响起那段熟悉的笛声。
不是通过仪器捕捉,而是直接出现在脑海深处,像是某种跨越维度的低语。
她忽然明白??沈知白并未消失,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他是每一次质疑背后的勇气,是每一滴泪水里的清醒,是千万人齐声说“不”
的那一刻所汇聚的灵魂震颤。
“他成了规则本身。”
她睁开眼,望向北方,“就像空气,看不见,却无处不在。”
就在此时,北方边境急报传来。
雁门关外,一支商队遭遇沙暴,迷失于戈壁深处。
粮尽水绝之际,领队的老镖师忽然取出一支破旧音笛,依稀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
奇迹发生了??狂风骤停,黄沙退散,天空裂开一线月光,照亮前方一条隐秘古道。
沿路石碑林立,刻着历代执灯者的名字,最末一块空碑上,隐约浮现一行新字:
**“待我归来。”
**
消息传回江南执灯塾,众人哗然。
有学者推测,这是“醒途之音”
在极端环境下触发的地脉响应;也有信徒认为,那是沈知白的意志仍在引导迷途之人。
唯有那位渔家出身的女讲师沉默良久,最终取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那盏纸灯笼,轻轻点燃。
火焰跳跃,映出她眼角的泪光。
她知道,那不只是传说。
那是真实。
数日后,朝廷派出特使前往江南,带来一道密旨:皇帝欲重启科举,广召天下贤才,尤重“心志清明、不受幻惑”
之士。
诏书中特别提及:“凡参与‘灯种计划’者,皆赐‘鸣心贡生’身份,可直入殿试。”
消息一出,举国震动。
许多人不解:为何偏偏此时重开科考?毕竟战乱虽平,民生未复,百废待兴之际,理应先修水利、赈济灾民,而非大兴文事。
但只有少数人懂。
林晚照接过圣旨时冷笑一声:“他们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