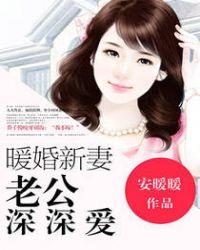宝书网>综武:我家娘子是状元李兆廷txt电子书 > 第576章 镇国公家有河东狮威严赫赫(第1页)
第576章 镇国公家有河东狮威严赫赫(第1页)
临近春闱,按理来说,国子监的太学生应该寒窗苦读,努力备考。
虽说今年是恩科不是金科,但考中了照样能做官,对于那些屡试不中的秀才而言,恩科是难得的大机遇。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努力备考的太学生。。。
林昭起身,将灯芯笔轻轻插进院角的泥土里。
那截焦黑的骨笔刚一接触地面,便有细小的根须自其裂纹中蔓延而出,如同活物般扎入大地深处。
他没有惊讶,只是静静地看着,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幕。
十年前清婉焚身时,火光映照下的长明灯残骸也曾这般悄然生根??不是死亡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夜露渐重,草尖凝霜。
阿蛮伏在门槛边,额间朱纹已不再闪烁,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微弱却稳定的银线,自眉心延伸至鼻梁,宛如文字初成的刻痕。
它睁眼望向林昭,瞳孔深处浮现出一行转瞬即逝的古篆:**“言出即种,种下即生。”
**
林昭轻叹一声,转身推轮椅回屋。
木门合拢之际,风从檐下穿过,吹动了堂前悬挂的一卷残帛。
那是《补遗》最后一页的复制品,上面只写着一句话:
>“当所有禁忌都被书写,真正的自由才刚开始。”
翌日清晨,书院钟声未响,孩子们却已齐聚院中。
他们围坐在泥地旁,盯着昨夜林昭写下的字迹??如今那些字已不再孤立存在,而是如藤蔓般延展,缠绕成一片低语般的纹路。
一个六岁女童蹲下身,用手指轻触“懂了就好”
四字,忽然咯咯笑起来:“它在动!
像蚯蚓爬!”
话音未落,那字迹竟真的微微扭动,化作一只由墨点构成的小虫,沿着她的指尖爬上手腕,又在她掌心留下一个符号:一朵简笔桃花。
“这是……清婉奶奶给我的?”
女孩瞪大眼睛。
林昭坐在槐树下,目光温和:“她没给你,她只是认出了你。”
众人不解。
哑僧缓缓起身,走到女孩面前,以手为笔,在空中划出三道弧线与一点。
盲女乐师立刻拨动琴弦,奏出一段清越旋律,恰似春雨滴落瓦檐。
林昭点头:“她说的是‘问’字。
古体‘?’,门中有口。
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门,而开口说话,就是推开它的力量。”
孩子们面面相觑,随即爆发出欢呼。
有人开始在地上乱画自己理解的“问”
,有人模仿阿蛮的样子用鼻子蹭地,试图唤醒沉睡的文字。
一个小男孩突然跳起来喊:“我梦见图书馆了!
那个穿白衣服的姐姐让我选一本书,我说我要看《为什么天会下雨》,她就笑了!”
林昭心头一震。
这不是第一个做这个梦的孩子。
过去三个月,已有十七名学生在入睡后描述过相同的场景:高耸的书架、旋转的楼梯、中央一盏将熄未熄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