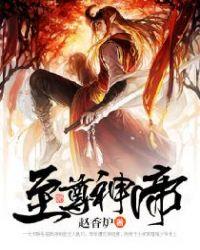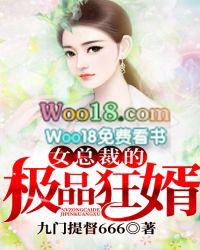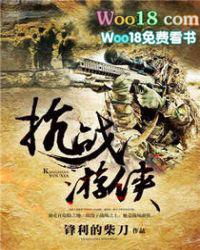宝书网>大明兽医,开局给朱标续命许克生小说百度云 > 175 和公主四目相对(第2页)
175 和公主四目相对(第2页)
箭身上缠着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条,以血书写:
**“北平棺不开,龙骨自归来。”
**
朱标拾起纸条,面色沉静如水:“胡守贞虽灭,但他种下的因还未尽。”
清扬咬牙:“这是恐吓!
他已形神俱灭,哪来的传讯?”
“不。”
朱标摇头,“这不是他的意思,是有人继承了他的念想。”
他望向北方,“燕王旧部,尚未肃清。”
翌日清晨,兵部急报:北平守将奏称,观澜阁地底异响连日不断,守陵军士夜间常见白光冲天,且附近村落孩童接连梦魇,哭喊“母后唤我”
。
更有樵夫言,曾在深夜见一披发女子立于山巅,怀抱婴儿,低语呢喃:“儿啊,娘等你接我回家。”
李景隆匆匆入殿,脸色铁青:“殿下,此事若传开,必又起流言。
是否派大军封锁观澜阁,掘地三尺,彻底毁去燕王生母棺椁?”
朱标闭目良久,缓缓道:“不可。
越是强行镇压,越会激起民间悲情。
百姓不懂政争,只知孝道。
若我们毁其母坟,便成了不仁不义之人,正中敌手下怀。”
“那该如何?”
李景隆焦急。
“我去。”
朱标睁眼,“以太子之尊,亲往祭奠。”
满殿哗然。
“你疯了?”
清扬失声,“那是他们的局!
明知危险还主动踏入?”
“正因为是局,才更要破得光明磊落。”
他起身踱步,声音低沉却坚定,“当年太祖迁葬空棺,本就有难言之隐。
与其任谣言滋长,不如揭开真相。
若燕王生母真在那里,我便以皇室礼迎回金陵,昭告天下,彰显仁孝;若不在……那就让所有觊觎者死心。”
七日后,銮驾启程,百官相送。
朱标身穿素袍,不带仪仗,仅率五百精锐护卫,携清扬、董桂花同行。
沿途百姓闻讯,纷纷焚香跪拜,非因迷信,而是感激《仁政十六条》施行以来,赋税减免、瘟疫得控、孤寡有养。
许多人含泪高呼:“太子仁德,万寿无疆!”
这一声声呼唤,竟隐隐形成一股温润气流,环绕銮驾而行,仿佛无形护盾。
抵达北平时,已是深秋。
观澜阁孤峙城北,荒草没膝,残碑断碣遍布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