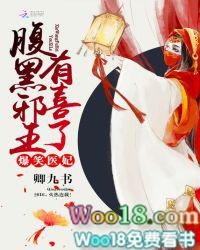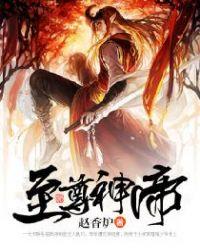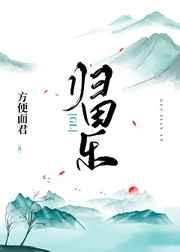宝书网>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小说TXT精校版 > 第868章 下播之后会干嘛我都不敢想(第4页)
第868章 下播之后会干嘛我都不敢想(第4页)
林晓阳没有打断,也没有说教,只是按下录音键,轻声说:“你说吧,我听着。”
后来才知道,那是李锐第一次完整讲述自己的恐惧。
两周后,他父亲在儿子劝说下参加了戒酒互助会。
临走前对袁婉青深深鞠躬:“我以为我不配做个父亲,但现在我想试试。”
年底将至,“非典型家庭节”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展厅中央搭建起一座象征性的“桥”
,由上千封信件折叠而成,横跨两侧展墙,一侧写着“出发”
,一侧写着“归来”
。
观众可沿桥行走,在中途投入语音明信片,系统会随机播放他人留言,形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布展期间,许雯悄悄送来一件展品??林晓阳十五岁时写给她的情书,字迹稚嫩却真挚:“我喜欢你看书的样子,像春天落在窗台上的阳光。”
她附言:“这不是爱情的终点,而是成长的起点。
我们都曾年少莽撞,也都值得被原谅。”
开展前一天夜里,袁婉青独自留守中心。
她打开所有录音设备,依次播放这一年收录的声音片段:王小舟奶奶的咳嗽声、唐果的第一句完整话语、阿婆念信时的颤抖嗓音、李锐在沙滩上许愿的童声、还有父亲读信时那一声哽咽的“对不起”
。
声音交织如河,流淌在整个空间。
她忽然想起十三岁那晚,自己蜷在沙发上发抖,渴望有人来盖一下滑落的毯子。
如今,她成了那个为别人掖被角的人。
凌晨两点,手机亮起。
是陈默发来的消息:“出版社确认,《声音档案》明年三月全球首发。
封面要用你折的那只纸船。”
她回复:“加上一句题词吧??‘所有未抵达的言语,终将在某处靠岸。
’”
雪又下了起来,轻轻覆盖城市。
她走出门,在“漂流信箱”
前驻足,放入一封信,没有署名,只画了一艘扬帆的纸船。
天快亮时,第一个晨练的老人打开信箱,取出信,眯眼看了看,笑着摇头,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便签,写下:“小姑娘,船要走得远,得有风才行。
我给你加个帆吧。”
他折了只小纸帆,夹进信里,重新投递回去。
就这样,一只船,两张信,三次流转,最终被唐果捡到。
她把它贴在教室墙上,带着十几个孩子一起画风、画浪、画远方的灯塔。
袁婉青站在窗外看着,眼底温热。
她知道,这场关于倾听与回归的旅程,才刚刚开始。